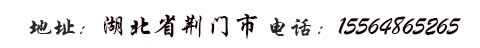刘剑梅专栏middot经典读札之
|
治疗白癜风的有效方法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130626/4197040.html 博尔赫斯是隐喻之王,他的文学意象非常丰富,结合了抽象的思索和天马行空的幻想,神秘深远,所以关于他的解读是无止境的。用格非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有多少博尔赫斯的读者,就会出现多少种对博尔赫斯的误解。”残雪写了一本《解读博尔赫斯》,是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灵魂探索,解读得非常精彩,既为读者揭示了博尔赫斯的心灵魔术,也让我们看到她在那座心灵迷宫漫游和冒险的脚步。批评家纷纷指出博尔赫斯小说和诗歌中最常出现的几个意象,如镜子、蓝虎、图书馆、匕首、高乔人、迷宫等,但是对我来说,最能揭开他的心灵迷宫的钥匙应该是“梦”。通过“梦”,他自由地穿梭于现实与虚构、抽象与具象、文学与哲学、短暂与永恒、生与死之间,构筑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第三艺术空间。阎连科曾经这样描述:“博尔赫斯带来了一种镜花水月的虚无感,一种人生无常、世事莫测的梦幻感觉,从真实中引出梦境,再从梦境中引出真实,如梦幻般模棱两可。这样,他就在现实和想像这两个空间之外,为后人搭建了第三个讲故事的平台:梦。”的确,梦是博尔赫斯召唤出的古老的魔术,是他接近永恒的途径,也是他对艺术和文学本质的定义。 博尔赫斯的梦就像他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所想象的“特隆”世界一样,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和唯灵的,是虚无主义的,带有浓厚的幻想文学色彩,以玄思神游为出发点去感知和想象整个天荒地老的广博悠远的宇宙世界。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有形的宇宙是一个幻影,而那看不见的需要通过潜意识去感知的神秘世界反而是实实在在的。特隆世界的本质就像残雪所阐释的:“特隆是一个幻想的王国,它同一切世俗的规范都不相干,人在凝视中看到的模糊景象是无限的创造力的涌动,是‘无’和‘有’的纠缠,是丰富到极点的混沌,是限定与突破的统一。”这段话一样可以概述博尔赫斯的艺术世界。就像特隆的玄学家们,博尔赫斯不追求真实性,也不追求逼真性,他所寻求的是惊奇和神奇。他总是驰骋于现实与虚构的模糊地带,在灵光一闪的瞬间,展示比现实和理性更为宽广和神秘的世界。即便他的小说充满了哲学内涵,俱有无穷神性的宇宙观,他仍是用幻想文学作为翅膀,来飞离被概念束缚的牢笼,所以他所营造的小说世界,让工具理性变得毫无用武之地,也让学院派的学者试图用来评论他的政治话语变得词不达意,唯有懂得心灵密语的艺术家,才能够与他共享那个不断衍生的无穷大的神秘宇宙世界。他在特隆世界中举了一个例子:“门槛的例子十分典型:乞丐经常去的时候,门槛一直存在,乞丐死后,门槛就不见了。有时候,几只鸟或一匹马能保全一座阶梯剧场的废墟。”这个例子有中国写意画的韵味,富有禅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心的影像里看到生命的处境,哪怕只有残缺不全的对物质的勾勒,完整的物的灵还存在,一样能够唤起读者思念天地之悠悠的宇宙感。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运用了许多奇特而怪诞的“魔幻”的手法,但是他在《百年孤独》中所虚构的马孔多,仍旧是现实社会的“镜子城”,是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缩影,所以他的家国情结和乡土情结比较重。相比之下,博尔赫斯则完全超越了家国情怀,而是典型的世界主义者,甚至是宇宙主义者。他的小说里不仅有西方世界,也有东方世界;不仅有现实世界,也有古今中外书籍中的世界;不仅有醒来时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也有梦幻中的潜意识世界。他的“梦”的意象,跟他的“镜子”的意象一样,都是他试图拓展和延伸现实世界的努力。他不满足于现实的单一维度,他的灵感来源于对古今中外鸿篇巨制的大量阅读,他可以自由地跟隐藏在世界文化历史书籍中的精灵们展开对话,借助“梦”的桥梁,他把抽象变成具象,把自己的思想用幻想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很喜欢邓恩的《时间试验》,因为邓恩说做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某种低微的个人永恒”:“做梦的人瞥一眼就能看到,就像上帝从其广漠的永恒看到宇宙间的一切过程一样。醒来时又将会怎么样?就像我们习惯于延续不断的生活一样,我们会给我们的梦以叙事的形式;然而我们的梦是多重的,是同时发生的。”博尔赫斯认为世界文学的所有经典作品都是精彩的“梦”,梦是幻想,是文学创作,是最古老的美学活动,是可以包容宇宙一切过程的最自由的艺术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是多重的,对自我的认知也是多重的。面对无穷大的不断衍生的梦,他一方面用怀疑的态度来质疑世俗世界中的所谓真理,另一方面他也真切地感到一种面对超自然和虚无的个体恐惧感。当他把梦以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梦就变成为了他独有的美学作品,既可以令他徘徊于存在与虚无之间,展示一种与天地合一、与万物等量齐观的透视力和感悟力,又让他像但丁在《神曲》中一样,对人内心的黑暗——“地狱的裂缝”进行奇妙而丰富的灵魂探索。 一 博尔赫斯对《一千零一夜》情有独钟,比如他的短篇小说《南方》中的主人公达尔曼在其命运转折之前,手里拿着的就是一本不成套的魏尔版的《一千零一夜》,后来达尔曼踏上回南方的旅程,手里拿着的还是这本神奇的书。《一千零一夜》那么吸引他,是因为这本书代表了变化万千、取之不尽的文学故事与文学之梦,拥有永不枯竭的创意和想象。阎连科曾经这样解读:“《一千零一夜》作为另一种元小说在《南方》中的对应与存在──回到《南方》的文本本身,《一千零一夜》在小说中的出现,不是一种道具与藉助的意义,而是另一种元小说的意义。”把《一千零一夜》看成是一个“元小说”的元素,就意味着它是小说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跟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有着相应的对话。博尔赫斯的小说常常来源于他在书本里的阅读经验,从书籍中发现另一个想象的世界,然后又重新创造这一世界,属于叙述中的叙述,想象中的想象,迷宫中的迷宫,梦中之梦。他有一首诗,题为“《一千零一夜》的比喻”,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甚至觉得他似乎在概述自己小说中的比喻,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比喻就是“梦”。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梦见隐秘的东方大门 或者已成灰烬的花果园, 人们还会做同样的梦, 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 正如伊利亚派学者的悖论, 一个梦化为另一个,生生不息, 进行着无用的交织, 织成了无用的迷宫。 书中之书。 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一千零一夜》的散文里,不仅提到这本书带给他的东方神秘性是无穷无尽的,也强调梦是《一千零一夜》偏爱的主题。他在文中谈到了《一千零一夜》中的两个人做梦的故事:一个开罗居民在睡梦中梦到有人让他去波斯的斯依法罕寻找宝藏,等他历尽艰辛万苦到了斯依法罕,可是那里的法官却反讽地告诉他,他梦见过开罗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宝藏,后来开罗居民回到了开罗家里,果然在他自己家的花园里找到了埋在那里的财宝。这个故事后来又被博尔赫斯改写成了短篇小说《双梦记及其他》。《一千零一夜》对于博尔赫斯的意义,不仅因为其神秘性,更是因为文学比现实世界多了一个维度,可以让人在文学世界中超越人生的困境。他写道:“一个人希望丢失在《一千零一夜》中,他知道,进入这本书就会忘却自己人生的可怜的境遇。”而他著名的小说《南方》果真就借助《一千零一夜》而达到了一个双重的世界。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写的就是一个双重世界:既是现实,又是梦,完全超越了我们熟悉的因果关系,达到了一种人生即梦的情景。主人公达尔曼有一天突然发烧,医院后,医生诊断他得了败血症,在手术后的日日夜夜,他似乎活在地狱和梦魘中,生不如死,身体仿佛不属于自己,只能任人摆布。可是故事发展到这里,博尔赫斯笔锋突然一转,很快就写到医生说达尔曼可以出院了,于是他就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准备回到他在南方的庄园。在旅行的路上,他又带上了《一千零一夜》──梦的隐喻,博尔赫斯还特地交代了达尔曼带这本书的目的:“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这本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被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在此,《一千零一夜》是令博尔赫斯可以跨越现实和梦境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有了它,所有难以想象的超越世俗日常生活的梦幻般的场景都会自然出现,而且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在火车上,达尔曼在冥想:“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到,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坐在行使向南方的火车上的达尔曼,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这一路程带有梦的色彩,打破了直线性的时间观:“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后来,火车突然在一个他不认识的车站停住,他下了火车,四周是一片荒野,他走进了一间杂货铺。接下去发生的故事,果然让人感到时光倒错,很像美国的西部片,达尔曼自己坐在杂货铺里孤独地喝酒,可是店里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粗鲁的人要跟他打斗。正当达尔曼不知如何应付的时候,“蹲在角落里的那个老高乔人(达尔曼身上看到了自己所属的南方的集中体现),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在此,高乔人是城市人对过去怀旧的象征,是都市生活中已经流失的久远的神话,是富有勇气的男子汉的符号。不过,这时候的达尔曼依然是两个人,一个向往着富有英雄气质的死亡,拿着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另一个还想着“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在我头上”。 这篇小说的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其实是相当模糊的,读到最后的结局,我们仿佛明白,达尔曼的南方之旅只是他在疗养院里做的一场梦,虽然整个旅程写得充满现实感,许多小小的细节,比如咖啡馆里的猫,都为了增强这种真实感而小心翼翼地铺垫着,可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原来这趟前往“南方”的旅程就是病人达尔曼为了超越现实做的一个梦,是一个类似《一千零一夜》中的文学故事:“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这种梦想成真的结尾就是博尔赫斯心目中文学应有的样子。南方是达尔曼的梦中之乡,尤其在他的身体被疾病束缚的时候,南方更是给了他梦想和希望,那个拿起匕首、义无反顾地走向决斗和死亡的硬汉子,只有文学里才存在,只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才存在,现实中的他其实还待在疗养院里,面对着人生困境,无奈地被自己的身体所囚禁。 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描写了“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富内斯是一个拥有超凡记忆力的人,仿佛连历史中的每一片树叶他都能记住,可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发生在生活中的一场灾难之后。19岁那年他从马上摔下来之后,“他生活过的十九年仿佛是一场大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性特大,什么都记不住。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他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时,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即使他已经瘫痪,可是他的记忆让他似乎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富内斯说:“我一个人的记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记忆的总和。”他的身体虽然被监禁在轮椅里,可是他的精神却可以在古今的记忆中自由地驰骋,无论是伦敦和纽约以往的辉煌,还是沸腾现实的热力,还是古老的知识和语言,各种各样的细节都在他的脑海里清晰地呈现。叙述者“我”觉得富内斯“像一尊青铜雕像,比埃及更古老,早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存在。”类似于《南方》中的并置──被疾病折磨的身体与浪漫的梦想,博尔赫斯展示了富内斯的双重世界:一方面是他哪里都去不了的身体,以及他必须面对的无奈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他却拥有那么丰富的精神资源,像一个精神超人,一个完全不被现实束缚而获得精神大自由的超人。而这样的双重世界恰恰就是文学的隐喻,就像卡夫卡笔下的煤桶,会带着主人公从困窘的现实困境中飞起。 二 博尔赫斯的梦跟艺术家的心灵创作过程紧紧相连,他似乎通过梦来谈论作家苦思冥想时的思绪,其创造时的痛苦与喜悦,以及创造时应该拥有的心灵状态。他的能够进入梦的最彻底的虚无深处的小说,应该是《环形废墟》。这是一篇典型的关于“梦中之梦”的故事。这篇小说里,一位来自南方的沉默寡言的魔法师来到被焚毁的庙宇的遗迹,在这个环形场所,他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睡觉做梦。“引导他到这里来的目的虽然异乎寻常,但并非不能实现。他要梦见一个人:要毫发不伤地梦见那人,使之成为现实。”开始他的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梦境起初是一片混乱,后来他梦见他自己在环形阶梯剧场给许多学生讲课,但很快学院就变形了,这个梦等于失败了,就像作家构思的一个作品半途而废一样。等魔法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后,他几乎马上梦见了一颗跳动的心脏,接下来的几天他慢慢梦见了一个个重要的器官,然后逐渐地,他梦见了一个少年,给予了他生命,并派他去另一座荒废的庙宇做拜火的仪式。自从有了这个来自于他的“梦的投影”的儿子,他夜里不再做梦了。不过他担心儿子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幻影。“魔法师花了一千零一个秘密的夜晚,零零星星揣摩出来的那个儿子的前途,当然使他牵肠挂肚。”小说的结尾,他思索的结局来得非常突然,火神庙宇的废墟再次遭到火焚,他朝火焰走去,可是发现:“火焰没有吞噬他的皮肉,而是不烫不灼地抚慰他,淹没了他。他宽慰地、惭愧地、害怕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这篇“梦中之梦”的故事,通过梦来像上帝一样造人的故事,仿佛博尔赫斯版的“佛兰根斯坦”,让人在梦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不仅儿子是幻影,而且魔法师也是他人梦中的幻影──好似文学的创作过程,在虚构的作品里,一切都是作者的梦中之人,梦中之物,一切都是幻影。佛教说的“四大皆空”,又何尝不是看清了人生一切皆幻影? 如果《环形废墟》展示的是一位作家进行精神创作的神秘过程,甚至是一位作家存在的虚无感,那么《神的文字》则展现了一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拥有的心灵的自由状态。《神的文字》中也一样提到了“一梦套一梦”和“套在梦里的梦。”一方面是永远被关在石牢里的巫师,一个束手无策的囚徒,永远都得不到现实中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他却通过“梦”而感受到了一种心醉神迷的与神和宇宙结合的大快乐。他见到了一个既是水也是火的无穷尽的轮子,这个轮子由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交织组成,他因此而感悟到了宇宙的隐秘,万物的起源,并且获得了无限幸福的感觉。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作家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内心拥有大自由,他就无所不能。它如同流亡文学里常常提到的“自我放逐”,即使身处暴君专制的国度,作家通过内心的自我放逐,也一样可以获得精神的大自由。这位巫师,即使他被囚禁在地牢里,当他感悟到自由就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他居然念出偶然凑成的口诀就可以“摧毁这座石牢,让白天进入我的黑夜,我就能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就能让老虎撕碎阿尔瓦拉多,就能用圣刀刺进西班牙人的胸膛,重建金字塔,重建帝国。”这很像庄子的《逍遥游》,而这口诀其实就是启开心灵自由的钥匙,关键还在于作家自己的意念──他是想要被现实所羈绊,还是想要获得个体精神的绝对大自由。这也是高行健所说的:“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 三 博尔赫斯曾经说过:“说到头,文学无非是有引导的梦罢了。”他的文学之梦有着自己独特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定义,喜欢把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安排得比较远,以便更自由地发挥想像。博尔赫斯有一篇非常神奇的小说《阿莱夫》,谈的是既是关于文学之梦的空间的定义,也是关于作家的视角和胸怀的问题。在小说之前,他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的句子:“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这句话揭示了文学的秘密,那就是,文学有“梦”的翅膀让我们拥有无限的空间。藏在地下室里的阿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从各个角度看到的、全世界各个地方所在的一点”。它的直径大约只有两三厘米,可是宇宙空间都保罗其中,所有的灯盏和光源也在其中。透过它,可以看到宇宙的任何角度,大到浩瀚的海洋,小到地上的蚂蚁,甚至看到逝去的情人以前写的信。“……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这个隐藏在地下室的阿莱夫,是博尔赫斯关于文学的最神秘的隐喻。他曾经说明,阿莱夫是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在犹太神秘哲学中,它象征着无限的、纯真的神明。其实,阿莱夫的隐喻就是“作家的眼睛”,作家的视野。优秀的作家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可以看到离家乡万里之外的实实在在的葡萄、地上的蚂蚁,以及女人的身体、过去的秘密等外在宇宙的每一个具体的存在,也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内心宇宙,甚至自我的内心世界,关键还在于,这个作家的视角是否是“宇宙的视角”。无论他住在哪里,哪怕只是住在狭小阴暗的地下室里,只要他拥有阿莱夫,拥有宇宙的视角,他就拥有包罗万象的世界和宇宙,而他的文学作品也会像宇宙一样宽广。 博尔赫斯的小说拥有宇宙的视野,区别于其他拥有乡土情怀和家国情怀的小说。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的:“我不知怎么福至心灵,会想到写直截了当的短篇小说。我不敢说它们简单;因为世上的文章没有一页没有一字不是以宇宙为鉴的,宇宙最显著的属性就是纷紜复杂。”正因为他有宇宙的视角,他虽然承认自己是保守党人,但是他的小说是超越各种党派纷争的,他没有让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拒绝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他认为:“我写的故事,正如《一千零一夜》里的一样,旨在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由于他拥有“宇宙视角”,他也像庄子的《齐物论》一样,在宇宙的观照下,现实中的善恶、是非、贵贱等二元对立消失于无形。对于他,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其实来源于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万物的本源,物之初,是虚无。因为是虚无的,所以万物是同一的,不需要纠缠在这些对立项中。比如他的小说《神学家》写到两位神学家奥雷利亚诺和胡安的纷争,两个人一个是正统,一个是异端;一个是憎恨者,一个是被憎恨者;一个是告发者,一个是受害者,在现实世界里他们纠缠斗争了一辈子,但是当他们到了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对于深不可测的神而言,他们构成了同一个人。这种超越正反、黑白二元对立的观点,也类似于中国佛教说的“不二法门”,只有拥有宇宙极境的眼光,才能超越这样的二元对立之争。他的另一篇小说《扎伊尔》通过一枚普通的钱币看到事物的正面和反面,让那个普通的钱币“扎伊尔”,变成透明的,两面都不重叠,而景象变球形,扎伊尔出现在球的中央──这样的描述是为了令读者从一个细小的东西看到包容万象的宇宙,看到涉及到宇宙的正与反、是与非的历史景象和生命景象,以及无穷的超越因果的复杂关系,而不被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法所局限。 四 博尔赫斯喜欢在小说、诗歌和散文中写他自己,不过他笔下的博尔赫斯可是千变万化的,是拥有多重主体的。他在一首《我就是我》的诗里曾经这样描述自己: 我是我自己看不见的躯体和面庞。 我是残阳将尽,那个听天由命的人, 用与众稍有不同的方式 摆弄卡斯蒂利亚语的词句, 叙说寓言故事, 穷尽所谓的文学 ……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回声, 希望无牵无挂地死去。 我也许是梦中的你。 我就是我。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博尔赫斯之所以千变万化,是因为他对自我的认知常常通过梦来实现,而文学本身就是无数的梦──过去的梦,现在的梦,将来的梦,梦中之梦,“梦的深处仍是梦”,即使完全失明也不影响他继续做梦,而梦中看到的一切比现实本身还更真切更完整,集个人经验、文学记忆、古老神迹于一体。正如他在一首《梦》的诗里所说的:“我比尤利西斯的水手们航行得更远,/驶向梦的境界,/超越人类记忆的彼岸。”以前阅读博尔赫斯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倾心于他有如图书馆一样的博学,可是最近重新阅读他的小说和诗歌,我更加明白,“梦”既是他对文学的定义,也是他寻找那个隐藏在书本中的多重自我的途径之一,或者说,他所阅读的所有跟他心灵相通的前人,都构筑成了他内心的一部分。他就像庄周梦蝴蝶一样,不知是文学中的人物梦见了他,还是他梦见了梦中的人物。“我将是众人,或许谁都不是,/我将是另一个人而不自知,/那人瞅着另一个梦──我的不眠。”“或者,还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我/我曾经到那贪婪的镜子里/去寻找过那如今已消失了的幻象的我?/也许,只有待到死了以后/我才能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名字还是真的存在过。”在一篇散文《博尔赫斯和我》里,一个拥有“世俗角色”的博尔赫斯和一个拥有艺术家的“本真角色”的博尔赫斯展开有趣的对话,但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是博尔赫斯本人,是他的双重主体。 每次谈到时间时,博尔赫斯都会谈到著名的赫拉克利特的小河。“他「赫拉克利特」说过的话我经常引用: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为什么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首先,因为河水是流动的。第二,这使我们触及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他好像是一条神圣而可怕的原则,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条河流,我们自己也是在不停地流动。在博尔赫斯看来,时间问题比任何形而上学的问题都跟我们紧密相关,当我们像赫拉克利特一样,看着河流中自己的倒影时,不仅这河不是原来的河了,赫拉克利特不再是原来的他,而我们也不再是原来的我们了。于是博尔赫斯发问:“我是谁?我们每个人是谁?我们是谁?也许我们有时知道,也许不知道。但与此同时,诚如圣奥古斯丁所说,我的灵魂在燃烧,因为我想知道时间是什么。” 他在两篇小说里──《另一个人》和《年8月25日》──都采用同样的“元小说”的叙述手法,让一个博尔赫斯邂逅另一位博尔赫斯。《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沙之书》中的一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年2月,不满二十岁的博尔赫斯在剑桥市的查尔斯河边遇到了头发灰白的七十多岁的博尔赫斯,两个人展开了有趣的对话。他们谈到自己喜爱的文学,可是发现昨日的人已不是今日的人:“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异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因此对话相当困难。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他们后来虽然约好了第二天再见面,可是谁也没有赴约。他们这次邂逅仿佛是相互做的一场梦,不过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一个不同的自我,自我可以是多重的、有差异性的,并不见得总是有连续性和因果性。《年8月25日》重复了这一主题,这一次刚满六十一周岁的博尔赫斯在一家饭店的19号房间遇到了即将死去的八十四周岁的博尔赫斯,他们觉得他们即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八十四岁的博尔赫斯对六十一岁的博尔赫斯说:“在拉丁语和维吉尔之中,你会完全忘却这奇怪的带有预言性的对话,它发生在两个时间和两个地方。当你再次做梦时,你将是现在的我,而你则成为我的梦。”八十四岁的博尔赫斯说完这话就死去了,六十一岁的博尔赫斯则逃出了房间,而他走进来时看到的所有景物如院子、桉树、塑像、凉亭、喷泉也随之消失了,仿佛一场梦幻。只有在梦中,“今日之我”才能与“旧日之我”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空间里邂逅,并展开对话,互相观察。博尔赫斯不仅领悟到多重性的主体,也对自我用怀疑的眼光进行形而上的批评、解剖和领悟:哪一个自我是真我,哪一个自我是假我?或者这些多重的自我都像《环形废墟》中的魔幻师一样,全部来自于虚无,并且走向虚无? 五 当然也只有在梦中,作家才有虚构时间的能力,打破直线式的进步的时间观。在他的小说《秘密的奇蹟》里,赫拉迪克是一位剧作家,被当局被捕后,他向上帝祈求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完成他手头的剧本《仇敌》。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晚,他梦见他去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找上帝,管理员告诉他上帝在图书馆四十万册藏书中的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他随手翻翻一本地图册,一个无处不在的声音告诉他,“你要求的工作时间已经批准”,这时他猛然醒来。第二天行刑的时候,士兵们突然一动不动,时间突然停滞了,他果然获得了一年的时间把剧本写完。在写完剧本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子弹突然飞来,这一次他真的被枪决了。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赫拉迪克做了好几次梦,通过梦,他把瞬间延长成整整一年,并用这一年的时间在死亡之前完成剧作。其实,上帝就是作家自己,他有虚构幻想的魔法来改变现实的时间,在自己的文字里把瞬间变成永恒。当然这被上帝批准的被延长一年的时间,也可以阐释为相对于“客观时间”而言的“主观时间”,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或许多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中都充满了作家和艺术家们虚构的“主观时间”。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曾经谈到故事时间的寓意性,即故事时间不能跟现实时间等量奇观。他谈到《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一个套一个,就是故事的时间不断扩张,这种在作品内部延长时间是为了躲避,躲避什么呢?当然是躲避死亡与终结。他也谈到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的时间观,谈到其中的多样化的多枝杈的时间的观点,仿佛任何现在都分成了两个未来,形成了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相互分离、相互交叉、又相互平行的不断扩大的时间网”,使得无限个宇宙可以同时存在。的确,博尔赫斯通过多变的梦,成功地实现向无限和永恒的时空的过渡。 虽然博尔赫斯看到作家有虚构时间、虚构永恒、超越瞬间的能力,他也探讨了是有限的人生更加珍贵,还是永恒的人生更加令人羡慕的问题。在他的小说《永生》里,那个“永生者之城”充满了神秘性,其实那位跨越了几个世纪的穴居人就是荷马,而叙述者“我”似乎在某一段时间也曾是荷马。作为读者,我们在几个世纪的梦幻般的传奇旅行中跟随着博尔赫斯一起思考着永生的问题。博尔赫斯认为永生者普遍受到因果报应的世界观的影响,所以他们失去了怜悯之心,他们对别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命运也漠不关心。相对而言,有限的时间赋予人们“死亡”,“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郁”,懂得珍惜转瞬即逝的生命。有限与无限似乎是一个悖论,人们因为有限的人生而向往永生,而永生的人却变成了“穴居人”,生老病死和进步的时间观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博尔赫斯揭示,真正能够“永生”的唯有文字,荷马就象征着所有载入文学史里的作家,也象征着永生的文学──文字和词语,它们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 六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蓝虎》里,那个讲授东方逻辑学的教师似乎真的去了恒河三角洲的热带丛林,又似乎只是做了一场梦,在一个被当地人视为圣地的山上带回了会自己衍生的蓝虎圆石,这个神秘的蓝虎圆石就是博尔赫斯小说中的“第三空间”的隐喻。它存在于高地上的隙缝之中,在《圣经》中它们象征着上帝的非理性,当地人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它的衍生与消失或者回归,完全没有任何秩序和规律可循。“这究竟是什么奇妙的空间,居然能吸收圆石,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一颗一颗地归还,遵循的是一些不可思议的规律或者说是惨无人道的决定?”这个不遵循人类熟悉的时间和空间规范的蓝虎圆石,是博尔赫斯构筑的独特的文学想像空间,它充满了偶然性,完全脱离了历史现实中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或因果论,极其富有创意。他所描写的那本无限的“沙之书“,或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通天塔图书馆”,都属于这个独特的“第三空间”──它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让拥有这个空间的人有时甚至感到恐惧与害怕。这个神秘的空间属于文学的世界,并叩问着个体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当一个渺小的个体面对浩瀚无边的宇宙时,他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博尔赫斯在一篇谈到但丁的《神曲》的散文《第四歌里高贵的城堡》中,提到地狱中的一个高贵的城堡。他说但丁的《神曲》只是他的一个梦,而但丁本人只是梦的主体而已。“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漆黑一片的丛林里不知所措,那里的梦何等深沉。”但丁在地狱里见到了四位既无悲哀又无欢乐表情的高大的鬼魂,那是荷马、贺拉斯、奥维德和卢卡努斯,这些赫赫有名的幽灵以“同行之礼”与但丁相见,并带他和维吉尔去那永恒的高贵的城堡。这些人在天主教问世前就已死去,似乎被上帝打入另册。但丁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城堡中,虽然在地狱,可是其实是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一个“第三地带”。博尔赫斯写道:“但丁不能置教义于不顾而拯救他的英雄们,便在想像中把他们安置在阴曹地府,远在天堂上帝的视野和支配之外,对他们神秘的命运深表同情。”《神曲》中描写的地狱里不允许诗人写作,于是这些鬼魂只好靠探讨文学来打发永恒的时光。在我看来,博尔赫斯在其作品中所营造的第三空间,似乎就像这座高贵的城堡──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现实世界的道德伦理规范根本无法描述这个空间,但它却是诗人与作家进行秘密的心灵创作的乐园。 博尔赫斯把文学创作等同于梦的虚构,梦即是他的美学。在创作中,他穿过“地狱的裂缝”去审视每一个灵魂,包括自己灵魂的黑暗面。他一方面感到艺术创作时的大快乐,就像《神的文字》中那位被关在地牢里的巫师,通过梦而有了顿悟后,会感受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与神和宇宙结合的大快乐,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常常提到梦醒后的恐惧感,当然这种恐惧来源于现实世界给他的压抑感,以及他面对虚无的无力感。无论梦带给他快乐还是恐惧,都是他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最真实的感知,都包含着形而上的思索,但不同于哲学的理性思辨,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文学对人的内在本性的认识。 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梦跟博尔赫斯的梦一样,也表现了人生即梦的主题,但是他所描写的“警幻仙境”和贾府的现实世界毕竟还是“彼岸”和“此岸”的关系,二者似乎并不存在于同一个空间,而博尔赫斯的梦则都在“此岸”,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自由而随意地穿梭于存在与虚构之间,把现实世界变得无穷大。梦,特别适合概括博尔赫斯小说的特性。第一,因为梦是多变的,随意的,捉摸不定的,无法预测的,与现实形成同构的关系,加上博尔赫斯对自己的小说有高度的自反性,有清醒的元小说的自觉,他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世界是繁复的多层次的,时空被扩充到无限大,让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第二,当梦的主体在现实和多变的梦境中游移,现实世界变得不再那么确定,而是充满了荒诞感和神秘感,梦的主体被一种淡淡的感伤和恐惧所笼罩,对人的本质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不由得产生深刻的叩问;第三,梦对于博尔赫斯,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是功能性的,是一种传输、转换,乃至于创造与再创造的机能。他梦幻空间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块石头都拥有永恒性和超越性,都与世界和宇宙连成一体,就像《永生》里的荷马一样,也像历史长河里留下的文字和词语。也就是说,博尔赫斯的梦都变成了世界文学的精品而获得了永恒,进入他心目中的天堂──图书馆。 本文首刊于《小说评论》年第1期,转载请标明出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s/5326.html
- 上一篇文章: 无删减版西藏绘画的流派之争副刊第9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