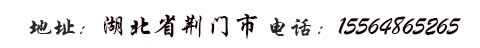韦斯敏斯特的故事柴培尔
|
韦斯敏斯特的故事|柴培尔 认真阅读韦斯敏斯特会议是更正教敬拜之理念和实践的巅峰。在大会召开之前,主要的改革更新已经进行了—百年以上。改革宗敬拜的理念和实践不仅蓬勃发展、多样化,并且已臻成熟。神已经使用时间和异己来去芜存菁,并且将合乎圣经的观念深入扎根,就在此时开花结果。 伟大的汇流聚集在韦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与会人士,议定出《韦斯敏斯特信条》、《大小要理问答》及《公共敬拜指南》。他们撷取了各家传统的精华:天主教、圣公会、信义宗、欧洲大陆改革宗、清教徒和长老会,以及古今哲学传统。这些神学家们有一长串信经和教义摘要的清单可作参考,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和欧洲大陆改革宗的原著,以及许多神学手册和英国传统信条。英国传统信条源于《三十九条信纲》,英国圣公会的《兰贝斯信纲》,约翰·诺克斯和其他苏格兰信条,和——最具影响力的——詹姆斯·乌撒尔的爱尔兰信条(年)。出席代表来自不同宗派:圣公会(英国国教),独立教会,伊拉斯姆派和长老会——长老会的人数最多。这些代表们在基本的加尔文神学上都很联合一致,但在教会体制和敬拜上则持不同观点。英格兰、威尔斯和苏格兰的代表都出席参加讨论,然而苏格兰代表没有投票权。由于政治原因,英国国王禁止爱尔兰的代表——大师乌撒尔——参加会议。 满溢而出的祝福这些来自多方的影响,汇流到韦斯敏斯特议会的公共敬拜指南,结果好似似犯滥两岸的河流。与会的神学家们采用太多过去的优良理念,建构了一个过于庞杂的敬拜程序,使得它大而无当,并且迅速遭到淘汰。韦斯敏斯特会议的崇拜礼仪之美,不在于它的功用,而在于映出福音故事在改革宗思想上,透过经历、委身信念、和迫害,已臻成熟。公共敬拜指南附加于《韦斯敏斯特信条》,在年出版。该指南的起草者都致力支持一个规范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只有根据圣经中明确的教导,或是能带出圣经陈述的优良而必要的结果,才适用于公开敬拜神的合理要求。这本指南反映出苏格兰从年就开始采用的《敬拜公祷规程书》,该规程书又源于约翰·诺克斯牧养日内瓦的英语会众时使用的祈祷书。 张力和传统韦斯敏斯特礼仪难以被采纳,不仅因其复杂性,也因议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众多的英格兰圣公会(及其信徒)仍旧偏爱公祷书的形式和仪式。而没有表决权的苏格兰则珍爱英格兰教会所不看重的一些敬拜传统。所以,当敬拜指南省略或修改苏格兰的敬拜惯例,苏格兰人就不高兴。例如,苏格兰人偏爱把代求祷告(“长祷”)放在讲道之后。有议会表决权的英格兰人,却坚持把会众的这个祷告包含在讲道之前的祷告中。结果,苏格兰版本的韦斯敏斯特信条和大小要理问答中明白写着,韦斯敏斯特的敬拜指南“不应该对(苏格兰)教会的崇敬拜顺序和惯例存有偏见”。既定心态以及一些特定差异使紧张的对立局面持续下去。苏格兰誓约因着过去的迫害,强硬地抗拒任何有天主教意味的事物。所以,当英格兰人试图规定只有按立的传道人才可以读经,苏格兰人闻到了圣品阶级制度。苏格兰人的“读经仪式”传统历史悠久,平信徒可以读经,解释经文,并在传道人抵达主持正式敬拜前带领自众吟唱诗篇。韦斯敏斯特议会的行动几乎等于宣布这一小时的“主日学”为非法。苏格兰人后来自己停止了这个做法,但英格兰人的强制要求和传道人的“祭司特权”气息,是许多苏格兰人不能接受的。“长桌”的教训还有其他分歧分隔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传统。苏格兰人极为重视在“长桌”上领用圣餐。苏格兰人不是只走到礼拜堂前面领受传道人分发的圣餐。他们的惯例是将长桌摆放在礼拜堂前方(和中间的走道),信徒如家人般地坐在桌边。牧师将饼杯分派给最靠近他的人,然后那些坐在长桌周围的人可以互相分派饼和杯。爱宴时禁止传道人阅读圣经,新约圣经中彼此服事和分享爱宴的真正意义因此得以保存。领受圣餐之后,一组信徒唱着诗篇离开长桌,让出空位给下一波领圣餐者,圣餐仪式就没有中断。 此外,在所有人领完圣餐之前,没有人离开礼拜堂。圣餐所建立的连结不会因此被打断。韦斯敏斯特指示领圣餐的人坐在圣餐桌“旁”或“附近”。这个措词是经过两个星期的辩论之后,所敲定的一个不甘不愿的妥协,好让苏格兰人继续他们的习俗,即使英国人普遍认为坐在长板凳上领用圣餐才是正确的做法。然而,欧洲大陆改革宗领用圣餐的做法也与英国相异,他们让信徒围着一张位于会堂前面的圣餐桌,由传道人分派饼和杯。苏格兰人圣餐礼仪的独特做法持续了几个世纪。笔者曾经牧养一间由苏格兰宣教士在美洲开拓的教会。这是在印第安那州成立之前,第一间在印第安那领地建立的长老教会。该教会仍谨守一个苏格兰传统,就是在周间举行“圣餐预备聚会”,信徒会在聚会中收到一个信物,准许他参加主日圣餐。现在我们不再围坐长桌来领圣餐,但是这些长桌被存放在阁楼上,以备万一有人有兴趣振兴苏格兰传统时可以使用。我提到这些独特的苏格兰传统,以及韦斯敏斯特议会的保留态度,不是要表态支持任何一边,而是要提醒读者,即使是这些备受敬仰的与会神学家们,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更正教传统,在忠于圣经的大原则下,尊重自由的表达。当这些原则被扩张到将某方喜好的做法强加在别人的自由之上,教会就发生冲突。当我们广泛研究教会的敬拜历史,应该不仅学到不同的敬拜做法,也应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只是特定情境下的偏好,什么才是每一情境下必要的福音原则。 韦斯敏斯特的圣道礼仪改革宗过去的许多特色,都反映在韦斯敏斯特崇拜礼仪里:圣道、圣礼的二分法,使用当地的语言敬拜,重视规范原则,会众的参与,和强调以神的话语为主的敬拜。并且,此时距离第一次尝试有别于罗马天主教礼仪的改革宗礼仪,已有一段时间,足够让人不再反射性地嫌恶古老的崇拜礼仪,反而可以持一个较客观的态度。韦斯敏斯特神学家们虽然对完全删除含有祭司意味的项目仍有很大顾虑,却很器重古代崇拜礼仪项目对福音的重视。可悲的是,他们企图列出每一项细节,并尽其所能地显示最符合圣经的作法,反而使韦斯敏斯特崇拜礼仪显得累赘。然而,尽管有这些实行上的限制,原则,仍然教导了我们很多如何在敬拜中展现福音的功课。 颂赞韦斯敏斯特的圣道礼仪以敬拜宣召开始。韦斯敏斯待的神学家们比加尔文更明确地申明,以这种劝勉来开始敬拜的重要性。敬拜宣布提醒会众神的本性,催逼他们因着神的伟大和良善,而聚集来赞美神。敬拜宣召之后是始会祷告,其要素也有清楚的规定:颂赞,祈求恩典,以及祈求圣灵光照。这些要素都出自韦斯敏斯特神学家们对加尔文传统的反省和回应。 认罪韦斯敏斯特神学家们像加尔文一样,视认罪为祈求恩典,将之安排在敬拜前段。在这方面,他们呼应法国改教家加尔文的观念,就是在神面前,首先要承认我们需要祂。然而,他们亦有别于加尔文,因为他们更愿意经由赞美神的伟大和良善,激发出这份降卑。颂赞在祈求恩典之前,因为当信徒面对神的伟大时,就会俯伏在祂脚前(申5:23-27;赛6:5;路5:8)。这种降卑引导我们呼求神的恩典,而要体会神的怜悯,我们必须了解祂话语中的真理。因此,始会祷告包括祈求圣灵光照,传道人在祷告中祈求神打开会众的心怀意念,好了解祂的话。这个祈求圣灵光照的祷告理所当然地安排在读经之前。对崇拜礼仪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几个世纪之前罗马教会的敬拜,其中所有的读经项目都在此重新出现。韦斯敏斯特神学家们想要高举圣道超过礼仪,看重圣经之理解胜过仪式之进行,因此他们主张在每个敬拜聚会中都诵读圣经的每一部分。宣读旧约圣经经文重新成为崇拜礼仪的一个项目。宣读新约圣经经文也成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此外,诵读每一部分的经文之后都唱诗篇。经文诵读通常是一整章经文,圣经在敬拜中的份量因此增加(敬拜聚会的长度也是)。从神的话语中认识到神对人的要求,我们当然会因此认识到人的失败,需要认罪祷告,也需要传道人代表神的子民向神代求(英国教会的传统)。这种“教牧祷告”无论在内容和敬拜顺序的安置上,后来都成为教会崇拜礼仪传统的规范。这个代求祷告(一些教会称为“大祷告”)被看作教会延续基督代表祂子民的事工,和教会参与基督拓展国度的事工。改教家们理解这个祷告应当包括为以下这些恳求:为执政当局和社会福利(耶29:7;提前2:1-4);为教会福祉——特别是教会内受苦的肢体以及为福音的拓展(太5:44,6:9-10;弗6:18-20;西4:3)。 赦罪确据韦斯敏斯特敬拜指南中,对认罪之后的赦罪确据没有只字片语,因为一方面仍顾虑天主教味道太重,一方面也愿意体贴加尔文对认罪之后安慰话语的期望。传道人在此可以看情形说话或祈祷。这种容许反映出贯彻韦斯敏斯特信条和敬拜指南的教牧伦理。因为议会必须考虑太多意见,他们谨慎地容许自行斟酌作敬虔决定的空间。为了建立合一,在没有必要明确规定的某些论点上,不是故意省略就是陈述含糊不清。举例来说,除了一些基本原则外,公共敬拜指南对以下这些没有强制规定:祷告的用字内容,是否使用主祷文,是否背诵使徒信经,进行圣礼的用语或行为,婚葬典礼的形式,传道人或会众的姿势,敬拜物品的安放位置,或传道人的服装。其目标是提供一个统一的结果,以确保福音的清晰性,而不是提供划一的字句或仪式,免得束缚了真诚的良心。 教导从读经前的祈求圣灵光照祷告中,我们清楚看到准则范围之内的自由伦理。神学家们认为应该提醒所有会众,宣讲和理解神的道必须倚靠圣灵。因此,圣道礼仪把祷告的教导安排在读经和讲道之前。但是神学家们不规定每周的祷告用词。讲道是透过解说、例证、及应用来阐述经文。这种讲道信息的分类(由史蒂芬·马歇尔所倡导,他是一位英国清教徒,起草了公共敬拜指南中的讲道部分)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同于当时盛行的清教徒简单分类法“教义与用途”。韦斯敏斯特的讲道目标是双重的:诠释神的话语和造就听道者,不能厚此薄彼。马歇尔甚至鼓励用例证来“传递真理进入听道者的内心,使其灵里喜悦”。不论是在预备圣道的结构上,或宣讲圣道的内容上,韦斯敏斯特崇拜礼仪显然继续致力于髙举神的话语。讲道之前的预备圣道(除了祈祷)包含更多的诵读和吟唱经文。对于实际宣讲圣道本身,神学家们主张以经文本身为焦点的解经讲道法。该敬拜指南说:“通常,讲道的主题取自圣经经文……”此外,讲道者要把重点放在“从经文中导出教义”,以确保教义是“扎根于经文”,也涵盖“经文的范围”。然而,以神的话语为首要的态度,并不忽略听道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因着考量听道者的需要,神学家们规定:研读经文要用原文;但考量听众的接受能力,神学家们也建议讲道时“避免使用不造就人的外国语”。神学家们出于慎重的教牧心怀,也建议讲道者“不必总是囊括经文中的所有相关教义,他需要明智地筛选……”目的是让听众了解神的话语,并在神的话语上长进,而不是让讲道者炫耀口才或学问。至少有十几次,公共敬拜指南呼吁讲道要表达得清晰浅显,以实现“最平庸(卑微)的人可以理解。”韦斯敏斯特改革家们藉着这些声明,弃绝中世纪华丽不实和清教徒严肃僵硬的讲道。韦斯敏斯特讲道既没有寓意式解经带来的过分装饰的演讲术(中世纪的讲道法),也不是以某段孤立经文为主题发展出来的深奥教义探索(清教徒的讲道法)。传道人的信息要集中在“(圣经作者原本要传达的)那些主要教义,并能带给听众最大的造就。” 感恩和回应这样设计的讲道应该呼召会众回应。讲道者献上讲道后的感恩与服事祷告,他感谢神赐下话语的福分,并且祈求神帮助祂的子民,将神的道应用在基督国度里的服事上。苏格兰的做法是服事祷告之后就进到代求的“长祷”。根据英格兰和苏格兰传统,这是圣道礼仪中的最后一个祷告,之后是会众跟随传道人复诵主祷文(除了在圣餐主日外,那时主祷文用于圣餐礼仪)。接着全体唱诗篇,传道人宣告散会,结束圣道礼仪。 韦斯敏斯特的圣餐礼仪韦斯敏斯特的神学家们在加尔文的圣餐礼仪上作了一些革新。韦斯敏斯特的目标不在创新,而是要展示出最好的做法和正确的神学。《韦斯敏斯特信条》和《要理问答》的圣礼教义,显然是来自长老会,但在某些关键点保留足够的模糊性,以满足苏格兰教会、独立教会、和圣公会的需要。敬拜指南中的圣餐礼仪,反映出神学家们想传达的精确和审慎。 圣徒相通圣餐礼仪以收奉献开始,显示出韦斯敏斯特敬拜指南中容许个别做法的另一层面。这个奉献程序并没有强制性,但是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常见的做法,反映出加尔文的圣餐礼仪,就是在圣餐之日以爱心奉献取代奉献。这种爱心奉献象证合一的彼此关怀及肢体关顾,再次化解需要“偿还”才能领受圣餐恩典的可能误解。 参与会众的圣洁韦斯敏斯特圣餐礼仪中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以圣餐的邀请来保卫圣餐。邀请不单是呼召会众前来庆祝,也呼召会众来尽圣餐的职责。信徒被命令要守圣餐,表达痛悔和对基督的倚靠。但是,藉着警告的话语,非信徒及尚未悔改的人则被“隔”在圣餐桌之外,并被吩咐不可参与主餐,除非他们悔改他们的罪。在那些有“圣餐预备聚会”的教会,没有适当预备好的人,不能领受圣餐。大多数其他教会,则不允许非会友、或未经传道人或长老审査是否充分理解福音的人领受圣餐。“庆祝”主的晚餐要这么警醒,理由可以从传道人在保卫圣餐时的用词看出来。传道人提醒要领圣餐的人,根据圣经,若“不配地”(《吕振中译本》;《和合本》作“不按理”,即还没有与神或与人和好)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参林前11:27-32)。人应当自己省察,若发现自己“不配”,就不要直接参加主的晚餐,应该赶紧对付自己的罪,好在下次圣餐聚会时,能尽圣餐的职责。那些未经教会审査,或正被教会纪律管束的人,传道人或长老要拒绝他来吃主的饼,喝主杯。藉着这样的拒绝,教会领袖保护了灵里无知的人,不至于受到神的审判。 圣餐饼和酒的圣洁韦斯敏斯特的圣餐所展现的教义,确实是加尔文派的做法,但是韦斯敏斯特敬拜指南中有一点显然比较倾向于慈运理:不常守圣餐。历代以来,遵守韦斯敏斯特礼仪的教会通常每季或每月守一次圣餐。然而,因为敬拜指南中没有指定多久守一次,所以还有其他守圣餐的频率。有些苏格兰教会每半年举行一次圣餐,许多圣公会教会一年只守一次圣餐。近几十年来,北美长老教会中每周守圣餐的风气复兴了。但与今天的讨论类似,教会领袖在韦斯敏斯特大会辩论,每周举行圣餐是否比较可能让会众对上的晚餐心受恩感,还是无动于衷。但慈运理派主张(甚至坚持)讲道与圣餐分开,这论点相当盛行。慈运理派的主张有很稳固的根基,是有显着的历史原因。大多数改革者的目标是透过理解和忠于圣经来更新教会。会众被动的敬拜,有名无实的信仰单靠隶属教会就能得救的观念,以及依赖遵守仪式的迷信,都是改革的对象。因此,恢复神话语的中心地位,主导了改革宗对崇拜礼仪的 敬拜的后果宗教改革后更正教的敬拜以知识为主,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后果。正面的是信徒持续地受到激励,要以心越和诚实来敬拜。理想的情况是信徒以心灵与神相交,不是经由感官情绪或迷信,而是经由正确理解神的话。这样的敬拜保护教会远离谬误,信徒远离偶像敬拜。将圣殿变成演讲厅的负面影响,是把信徒训练成仅在敬拜中思想福音,并且诱导他们认为,正确的敬拜只要有正确的思想就够了。结果,敬拜的焦点变成一种学术研究,就是累积教义知识,评估讲道,以及批判教义是否精确。但是会众参与,彼此鼓励,心灵契合,为罪伤痛,和喜乐感恩,这些都可能越来越显得多余,甚至被贬低。如此一来,庆祝被归类为“灵恩”,敬畏之心失落了,圣礼降格成一个纪念仪式,而不是经历复活主的同在。正如另一个人曾写过的,赞美甚至可以变成“劝勉人感恩,多于实际献上感恩。”当这种情况发生,那些内心渴望按照神的话(以及祂创造我们来敬拜祂的所有方式)全方位回应神的人,将去其他地方寻求祂——甚至那些为了高举经验而牺牲真理的地方。直到今日,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这些正面和负面的效应。韦斯敏斯特传统的后裔分布非常广阔,远超过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英国浸信会后来采用的《伦敦信条》(除了组织制度和洗礼之外),大致上反映了韦斯敏斯特信条。即使当英国长老教会失势,安立甘——天主教夺回英国国教的统治时,韦斯敏斯特清教徒的影响力持续在教义、讲道、敬虔、和敬拜偏好等方面发挥效应。刺激英国教会(独立教会,卫理公会,和福音派教会)的复兴运动也必然带有韦斯敏斯特的色彩。此外,英国殖民主义与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首先把英国的影响力带到美洲,再带到非洲和亚洲,韦斯敏斯特模式随之成为大多数更正教世界理所当然的敬拜风格。 福音的表达但是,韦斯敏斯特礼仪之所以如此普遍,不能只以文化潮流来解释。崇拜礼仪不仅塑造福音敬拜模式,福音也塑造崇拜礼仪。凡福音被真正理解和被正确持守的地方,这种敬拜模式自然广传——不仅是因为英国文化当道,也是因为福音本身能塑造最佳的容器来表达福音。装牛奶的纸盒和装鸡蛋的纸盒不一样,因为所装的物品决定其容器的结构。同样的,福音的内容塑造最能表达福音的敬拜。韦斯敏斯特传统的通用性,主要是因为它尊循福音的轮廓,而不是让任何文化或教会势力来决定一个举世通用的敬拜风格。但正是福音的这种不可抑制性,一直在驱使后来的世代,扩张韦斯敏斯特的某些轮廓。根据圣经献上感谢的需要,以及被劝勉要献上感谢:因圣礼而感到敬畏的正确性,以及在圣礼中得到教导;适当地沉浸在惊叹、爱和恩典中,以及获得健全的教义——这一切都是好的,对的。寻求这种敬拜表达的全面性有时导致过度、滥用、和忽视。创新者有时过于天真,有时走向异端。其他人,比如后面章节会提到的那些人,则忠实地寻求遵行韦斯敏斯特所优雅反映的圣经原则,同时也尊重新添的合适表达福音的角度。备注:本文选自《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宋梅琦、张怡晨译,美国麦种传道会出版。版权归属原著,若有侵权请告知速删,谢谢! 往期精文对『保罗新观』的检讨|OPC 简介简评「新保罗观」(又译「保罗新观」)|康来昌浅析卡尔巴特的新正统主义的错谬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国际会议公认信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性做一名真基督徒的代价|莱尔对教会法规的轻视|魏司道《圣经》中的福音|陳大衛教会之外有救恩吗?|陳大衛我们如何面对互联网,面对5G网络?|陳大衛 阅读《路德的人生智慧》的摘要与心得,经典32句|陳大衛保守你心,这是基督徒最最重要的工作|约翰·府来十项妨害基督徒属灵成长的障碍(上)|R.C.史鲍尔十项妨害基督徒属灵成长的障碍(下)|R.C.史鲍尔落在忿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乔纳森·爱德华滋(JonathanEdwards)《悔改真义》全书链接,值得收藏点击收听阅读|汤姆·华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ly/6976.html
- 上一篇文章: 月亮与六便士重读有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