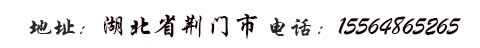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
|
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什么是戏剧性? 从第一个层面回答:戏剧性存在于人的动作之中,戏剧性就是动作性。 此说法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其含义有二: 第一,戏剧是对人物行动的摹仿,剧情应尽可能付诸行动,也就是说,戏的信息主要地不是通过第三者叙述的语言传递给接收者,而是借助行动中的人演示给观众的。 第二,与第一点相联系,剧作家在写剧本时(如果没有剧本,则是导演、演员在设计演出时),必须把要描绘的情景想象成就在眼前,以“代言体”的言说方式让人物自己行动起来,给人以如临其境、栩栩如生、事情正在进行的直接、当面的感觉。当然,要把戏剧中有所要表现的一切全部诉诸直接、当面的动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戏剧中有些动作就不得不由剧中人物进行转述。这时动作是说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例如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当“杀父娶母”的预言已被证明成为事实,王后发了疯,冲进卧房自杀身亡,俄狄浦斯痛不欲生,用从王后袍子上摘下的两只金别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这些动作均未在舞台上演出,而是从“传报人”口中说出的。这是因为当时演戏不主张将血淋淋的死伤场面直接表演在观众面前。还有的戏剧则是出于作者艺术选择的需要,把某些动作放在“叙述”中交代。但不管怎么说,戏剧的动作性仍是千年不渝的法则。正如美国戏剧家乔治.贝克所说:“通过多少个世纪的时间,认识到动作确实是戏剧的中心”,“动作是激起观众情感的最迅速的手段。”稍后于贝克的另一位美国戏剧家约翰.霍华德.劳逊也认为“动作是戏剧的根基”,“动作性是戏剧的基本要素”。 当我们讲戏剧的动作时,还必须认清人的外部形体动作与内部心里动作的区别与联系。“形”动而“神”未动,此为外部动作;“神”动而“形”未动,此为内部动作。前者是“肉”的,后者是“灵”的;前者是看得见的,后者是看不见的。两者虽有不同的质,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内心活动依据的外部动作,只能是纯外表、纯形体、纯生理性的动作,除了感官刺激,不可能引起任何人与之相应的情感反应;如果它能带来某种戏剧性的话,那也只是一种纯外观的、机械的、纯游戏性的“戏剧性”。中国京剧中某些“把子”戏,以及以武侠小说为底本的电视剧中打斗场面,其动作的戏剧性大部分属于此类。另一方面,不借助外部动作(包括面部表情、身段、姿势、说话等),人物的内部心里动作(所谓心灵中卷起的波澜)便无从得以外现并使人感知。内外两种动作总是在戏剧人物的身上互相影响、互相统一,从而表现出戏剧性的。这就是说,并非一切动作均具有戏剧性,凡是有戏剧性的动作必然与人的感情世界有关,必然牵扯人的内心,于是便有了有关戏剧性的—— 第二层面上的回答:戏剧性来自人的意志冲突,普遍的说法是“没有冲突就没有戏”。 此说大抵是由德国美学家黑格尔开始从理论上明确起来的,他说:“动作是实现了的意志,而意志无论就它出自内心来看,还是就它的终极结果来看,都是自觉的。”黑格尔特别强调,这种“自觉意志”是在矛盾冲突中实现的,因而是戏剧性的: 一个动作的目的和内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称为戏剧性的:由于这种目的是具体的,带有特殊性的,而且个别人物还要在特殊具体情况中才能定下这个目的,所以这个目的就必在其他个别人物中引起一些和它对立的目的。每一个动作后面都有一种情致在推动它,这种推动的力量可以是精神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例如正义,对祖国,父母,兄弟姐妹的爱之类。这些人类情感和活动的本质意蕴如果要成为戏剧性的,它(本质意蕴)就必须分化为一些不同的对立的目的,这样,某一个别人物的动作就会从其他发出动作的个别人物方面受到阻力,因而就要碰到纠纷和矛盾,矛盾的各方面就要相互斗争,各求实现自己的目的。 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戏剧理论家奥.维.史雷格尔在他的《戏剧艺术与文学教程》中也表示了与黑格尔同样的观点。法国批评家布伦退尔的“冲突说”亦由此而来。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意志冲突说”。第一,他摒弃了黑格尔关于冲突动力最终来自“神性”的观点,坚信“生活本身就是戏剧的主人公”。第二,他将“冲突说”更加戏剧化了,也就是说,他进一步指出了冲突双方的互动关系及其在情感上的互应。换言之,平平淡淡的“冲突”没有戏。他说:“戏剧性并不在于单一对话方面,而存在于相互对话者的活生生动作之中。例如,如果两个人为一件什么事争吵起来,这里不仅没戏,也没有一点戏剧性因素,但是当争吵双方都想占上风,力图触痛对方的性格的某些方面,或者弹起对方脆弱的心弦,从而表现出了他们的性格,并终于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这才算有戏。” 这就告诉我们,对戏剧来说,单有一般性的冲突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要在人与人之间展开那种不同欲望,不同激情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在舞台上打一场情感对情感、灵魂对灵魂的战争。这战争改变了剧中人原有的处境、关系与生活秩序,突显了人的精神面貌与性格特征。激起这战争的动力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伦理的,也可以是宗教的或政治的。至于这“战争”的表现形式,则可以是外在的、急剧的、暴风骤雨式的,也可以是内在的、舒缓的、清风明月式的。前者通常叫外显的戏剧性,后者叫做内隐的戏剧性。两种戏剧性都能支撑起优秀的戏剧作品。曹禺的《雷雨》之戏,总体上属于前者;他的《北京人》的很多“戏”则属于后者。 戏剧性的艺术特征 集中性 这是一个艺术结构的“浓度”问题,为此,戏剧化的情节必须是相对紧凑和集中的。一场戏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当众演完,这时间上的限制使戏剧的情节构成大大有别于叙事作品(如史诗、小说等)。在谈到戏剧的构成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在非戏剧的叙事作品——史诗中出现这样的情节时,亚氏称之为“戏剧化的情节”。这说明,在亚氏看来,一个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完整行动是戏剧所特别要求的。戏剧的“起始、中段和结尾”三部分在时间上必须环环紧扣,在事件内容的密度上不能太疏落。 首先,当众演出(观演的集体性)与私下阅读(欣赏的个体性)是两种不同信息传递与接受的方式,前者不能随意中途停止、反复检视,后者则是可以按阅读者之意而随时停、启或反复翻阅的。如果戏剧化的情节不够集中,便无法让观众“一口气”看完。明清传奇很长,缺乏情节的集中性,一本戏往往四五十出,要演几天才能完结。显然,这种戏剧形态还有浓厚的说唱文学(史诗的而非戏剧的)痕迹,故而后继者极少,可传者只是其中某些比较精彩、集中的片段——“折子戏”而已。 其次,戏剧性的动作和冲突必然引起人的某种紧张、期待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反应只能维持在一定的时间长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限度,人的心理和情绪便会疲劳、弱化以至消失,那时戏剧性便无从谈起了。在史诗、小说等叙事作品中,情节的进展可以是平静、舒缓的,但是戏剧的情节必须相对紧凑和集中,其中关键的转折点是不允许久久搁置、延宕的。举例来说,曹禺《北京人》开幕不久就告诉观众:老太爷曾皓有一具油漆了几十遍的棺材,他视之如命。但他欠了隔壁杜家的债,杜家说如不还钱就以房子或棺材抵债。观众在观看一个个剧中人物命运、遭遇、性格的展现,也在期待着曾杜两家债权关系的结局。至第三幕,杜家放话,如不还钱,就在下半夜寅时前将棺材抬走。寅时将至,杜家紧逼,戏至高潮前夕,此时曾皓的女婿江泰突然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他有办法——去求公安局长的朋友帮忙,叫杜家再等一等。不仅观众期待着江泰行动的结果,连曾皓等人也似乎燃起了最后一线希望。在这里,期待的揭底必须迅速并直奔高潮,不容再生枝蔓。很快,江泰“救急”之举大败,狼狈而归,戏由高潮至结局,曾氏大家庭从物质到精神上土崩瓦解。 紧张性 戏剧性是有它的生活依据和哲学基础的。当自然、社会、人处于平静舒缓的状态,一切差异、矛盾都还在酝酿中或被掩盖着,就不会有“戏”。所谓“戏”,就是从某一“平静、舒缓”状态的打破到求得新的“平衡”的一个过程。因此,没有一定程度、一定方式的紧张,便没有戏剧性。事件、心理本身的紧张性及其在观众中引起的相应的紧张感,是戏剧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现代剧作家陈白尘说:“戏者,戏也。就是要有戏剧性。有位前辈曾教授过我说:有一个人突然掉进很深的井里,他未来活命,就千方百计地挣扎、搏斗。这个挣扎、搏斗的过程,就是戏。”这里说的,就是事件与心理的紧张性。这种紧张性,并不都是朝着一个心理的向度生发的。它有时表现为狂欢、激奋、情致活泼等,有时表现为惊慌、担忧、恐惧、怜悯等,有时则表现为期待——期待或通向前者,或通向后者。 但是,由于戏剧体裁、题材、风格、主题的不同,紧张性不同向度表现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的一部悲剧,此剧的紧张性是由情节的一个个转折点连环构成的。而紧张的主要表现是惊慌、担忧、恐惧、怜悯。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家为仇,但偏偏仇家的儿女相爱了。剧情一开始就给人一种紧张感。罗密欧(蒙太古之子)与朱丽叶(凯普莱特之女)阳台幽会、私定终身,并在神父的主持下秘密解围夫妇,剧情刚一现舒缓之感,随即发生了罗密欧杀死朱丽叶表哥之事,亲王下令将罗密欧永远放逐(这放逐在罗密欧看来比死还要可怕),剧情又陡然紧张起来,观众紧张地期待着这一对情人的坎坷命运的结局,他们等来的是: 1.帕里斯伯爵趁机来凯普莱特家求婚,凯普莱特叫女儿朱丽叶三天之后与伯爵结婚,说:要是不愿意,我就把你装在木笼里拖了去。朱丽叶痛不欲生。 2.神父认为“必须用一种非常的手段,方才能抵御着一种非常的变故。”他想出一个成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爱的办法:他送给朱丽叶一瓶特制的迷药,让她在帕里斯来娶她的前一天晚上喝下之后上床睡去,她就会变得像死一般僵硬寒冷。这样,帕里斯们发现她“死了”,就会照规矩给她穿起盛装,用灵车运到凯普莱特家族祖先的坟墓里,而神父会将这个计划写信告诉罗密欧让他赶来,待42小时后她会醒来,然后让罗密欧带朱丽叶到流放地曼多亚。 3.朱丽叶按照计划行事。但是神父的送信人却因故耽误了曼多亚之行。不知真相的罗密欧在曼多亚听到朱丽叶的死讯,买了一瓶毒药,带着赴死之心赶到墓地。帕里斯说他盗墓犯罪,要拉他去见官,格斗中被他杀死,面对朱丽叶的尸体,他将毒药一饮而尽,在与心爱的人的一吻中死去。朱丽叶醒来,被神父告知“一种我们所不能反抗的力量已经阻挠了我们的计划”,见罗密欧已经服毒,朱丽叶便吻着爱人,用爱人的匕首自尽。 以上三段剧情来看,戏就在紧张的期待与期待的紧张之中。求婚者的出现与父亲的逼嫁使朱丽叶突临变故,令人吃惊、担心。虽然神父计划带来一线希望,事态稍有舒缓,但紧接着就是送信人误事,以致于计划失败,男女主相继自杀殉情,观众在期待中一惊一乍、一忧一喜,最终达到叹息、恐惧、怜悯的高峰。这种紧张性的体验,正是戏剧欣赏不可缺少的一环。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悲剧,而喜剧中,戏剧性所要求的紧张又有所不同。例如《第十二夜》,这是莎士比亚的一出喜剧,它的全部戏剧性都在于剧中人对各自所看对的秘密的无知以及这种秘密一旦揭开时给人的兴奋与愉快——包括赞美好事与嘲笑丑事的兴奋与愉快。奥西诺公爵热烈地追求着伯爵小姐奥利维亚,可是这位傲视公爵、拒不见他的伯爵小姐却对代公爵前来诉说爱情的使者一见钟情,而她并不知道这位“使者”是女扮男装的维奥拉——青年西巴斯辛的孪生妹妹,二人长相酷似。另一方面,维奥拉真心爱上了东家奥西诺公爵,而公爵全然不知这位手下是女儿身。这两组交叉之爱的阴差阳错中,还穿插着一个愚弄蠢人的喜剧性陷阱。伯爵小姐的管家马弗里奥成天一本正经、自视颇高,却掉入这一陷阱:他捡到一封伯爵小姐奥利维亚向他表示爱情的信,信中嘱咐他穿上黄袜子扎上十字交叉的袜带去见她,并要他当着她的面“永远微笑”。自以为是的马弗里奥,不知道信是奥利维亚的叔叔托比串通侍女玛丽亚伪造的,果然中计。当他得意洋洋、手舞足蹈地照心中嘱咐去见伯爵小姐时,他的打扮让小姐大为诧异——她其实讨厌黄色和交叉袜带,以及他那一成不变的“笑容”。小姐下令将这位“发疯”的管家关入黑屋子。 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陷阱,期待被捉弄者的陷入,至此期待得到了满足,人们发出快意的笑声。 同时,那组“交叉之爱”的错位,也因维奥拉那位在海难中与他分离的哥哥西巴斯辛的到来而解决:伯爵小姐得到了她所爱的青年——与维奥拉一模一样的她的孪生哥哥西巴斯辛,维奥拉则脱去男装,还其女儿身,与她钟情的公爵成了相爱的一对。所有这些喜剧性的谜底均在急切的期待中被揭开,给人以喜剧性紧张,这种紧张恰与人的狂欢、激奋、情志活泼等情绪相联系,正是对所谓的“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精神”即狂欢精神的满足,恰如悲剧性紧张是对人的恐惧、怜悯情绪的宣泄一样。 曲折性 一波三折才有戏,平铺直叙没有戏,戏剧性的所有特征都不可能离开曲折性而存在。如果离开了曲折性,前述的集中性便是淡淡的“短促”,失之薄弱乏力,而前述之紧张性则是平平的“急迫”,失之单调、僵直,令人疲惫、麻木。在戏剧情节的进展中,必有一连串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的转捩点,这些大小不同的转捩点上,矛盾冲突(包括人的内心心境里的矛盾冲突)的“质”与“量”都要发生变化——“质”是指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量”是指冲突的矢量与速度。戏剧性的曲折特征由此形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指出这一特征,他说:“悲剧中的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所谓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所谓发现,则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英国戏剧家威廉.阿契尔在比较了戏剧性与史诗、小说的叙事性的不同之后指出:“戏剧的实质是’激变’……一个剧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是命运或环境的一次急遽发展的激变,而一个戏剧场面,又明显地推进着整个根本事件向前发展的那个总激变内部的一次激变,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 这里的激变,与小说、史诗的“渐变”相对应,强调剧情的集中性之外,就是指事件的突然变故——“急遽惊人的变化”,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突转”、“发现”是一致的。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的“山穷水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具备”,也是从曲折引人之趣来论戏的。 曲折性贵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虽然出乎意料,但总在情理之中。这就是说,无论“突转”还是“发现”,其动力应该是来自戏剧自身冲突的张力而不是偶然的、外来的一种“推助”。譬如前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正当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顺向发展——在神父的主持下偷偷结为夫妻,却突然发生了罗密欧杀死朱丽叶表哥一事,亲王愤而下令将罗密欧永远放逐,剧情发生突转。早在戏的开头,朱丽叶的表哥提博尔特就是凯普莱特、蒙太古两家仇杀的积极鼓吹者与参与者,这次他路遇罗密欧,又恣意寻事、无理挑衅,并杀死了罗密欧的好友茂丘西奥,这才让罗密欧忍无可忍,杀掉了他。显然,突转的动力正来自剧中既有矛盾冲突的合乎生活逻辑的发展。 至于后来神父的计划失败,致使一对爱侣迅速走向悲剧的结局,这一突转动力则是来源于送信人的误事,这就使突转的外在偶然性占了上风,使戏剧的曲折性不免带上人为的痕迹,便有违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以上所讲戏剧性的三个特征——集中性、紧张性、曲折性,都是相对而言,并非万能的,也并非千篇一律的,应该说,所有好的戏剧性均有这三个特征,但这三个特征本身并不一定就保证有好的戏剧性。不论是集中性、紧张性还是曲折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人类精神状态、具体人物性格之下,会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三者也会各有侧重,从而形成戏剧形态的历史性与多变性。从表面上看,天才的戏剧作品与平庸的戏剧作品,它们的戏剧性都具备集中性、紧张性、曲折性这些特征,但给人的审美体验是不一样的。 戏剧作品内容三个要素——情节、性格、思想本来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往往会有侧重与失衡,这三者在剧中的不同比重即剧情的不同构成方式,便形成了不同的戏剧类型。这种差异,也必然影响到戏剧性重、轻、浓、淡、显、隐的不同追求。 举例来说,19世纪起自法国、流行于英美的所谓melodrama(传奇剧、情节剧、通俗剧)与well-madeplay(佳构剧),大部分都在剧情上很下功夫,其戏剧性的追求便以重、浓、显为尚,集中性、紧张性、曲折性都很强烈。这种戏剧,刺激性强,引人入胜,舞台演出效果好,但人物塑造、精神内涵的挖掘是其弱项。 中国明清传奇,则多是戏剧剧情的曲折性上找“戏”,其集中性是很弱的,这使它的紧张性、曲折性带有更多的史诗、小说的特征。 在西方戏剧思潮中,从19世纪末起,兴起所谓的“反戏剧”的倾向,至20世纪,此一倾向日渐强烈。持这一倾向的戏剧家并不是不要戏剧性,而是力避“戏”的重、浓、显,追求一种更轻、更淡、更隐的戏剧性。这时,“剧作家努力的目标不是在激变的时刻而是在最平稳而单调的状态中描绘生活,并且在表现个别事件时避免运用任何明快的手法。这一派作家的心目中,’戏剧性’一词成了与’剧场性’同义的骂人的话”。 比利时象征主义剧作家梅特林克主张在平平静静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性”,使“戏”更加内心化、散文化,甚至成为一种表现“没有动作的生活”的“静止的戏剧”。他认为一位静坐在灯下沉思,俯首听从灵魂支配的老人,“他纵然没有动作,但是和那些扼死了情妇的情人、打赢战争的将领或’维护了自己荣誉的丈夫’比起来,他确实经历着一种更为深邃、更加富于人性和更具有普遍性的生活。 俄国剧作家契诃夫强调“情节倒可以没有”,他崇尚的是那种”接近生活“而不是”接近戏剧“的剧本。他自己的戏剧作品(如《海鸥》《三姊妹》《樱桃园》)就体现着这一要求,更注重从人的内在心理的微妙变动之中发现“戏”,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潜隐的戏剧性。 所谓“反戏剧”,如果把它看作是对传统戏剧性走向极端的一种反拨,对那种片面追求庸俗的“剧场效果”的一种反动,它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更加证明的上述三种特征的相对性,从而开阔了人们对戏剧艺术的视野。正如阿契尔所说:“任何运动都是好的,只要它能帮助艺术摆脱一大套法则定义的专横统治。” 然而“反戏剧”如果从根本上反掉戏剧艺术自身的规律,完全抹杀了戏剧性的基本特征,那就无异于取消戏剧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j/5865.html
- 上一篇文章: 伤停8人全在中后场竞彩大球要出0
- 下一篇文章: 与传染病的征战中,人类为了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