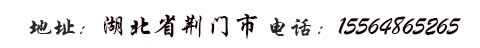小说欣赏穆middot巴兹杜尔吉波
|
北京湿疹医院专家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814669.html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有奖问答: 文学的绣布底下常常暗藏着历史的线索。今天我们为各位读者推送的《萨拉热窝》也是这样一块绣布。欢迎读者朋友阅读这篇小说,并回答问题:为何小说主人公斯特凡曾经如此痛恨萨拉热窝?答案不限字数。我们将从留言中评选出五个最佳答案,给获选者送出《世界文学》文创小礼品。活动截止时间为本周日晚8点(到时我们会将评论区的所有答案外放,并联系获奖者)。 萨拉热窝 穆哈莱姆·巴兹杜尔吉作高兴译 萨拉热窝,泥沼和雪做成 他对母亲说,他打算去斯梅代雷沃看看米丽卡。老太太听后还是蛮开心的。他们分手时,她很伤心。如今美国并不像过去那样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她说;有互联网这玩意儿,再说一年后她就能随咱们去了。他没有勇气告诉母亲,去美国其实并非导致米丽卡同他分手的缘由。 肩挎着背包,他朝泽雷尼·维纳克方向走去。他掏出钱包,再一次看了看巴士车票。蓝色车票上,印着“运输中心”几个字,用大大的西里尔字母写成。它们下面则是几个较小也较淡的字:“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三天前,他问过柜台后面的女子:有没有直达萨拉热窝的巴士。要多少有多少,女子回道。她正大口大口享用着皮塔饼之类的食品。我的意思是到市里,而不是到卢加维卡。女子,嘴里塞满了吃的,回答道,她并不为联邦政府售票。那就有什么,给我什么吧,他作出让步说。女子用沾满油脂的指头,嗒嗒嗒敲了几下键盘,然后抬起头,第一次看着他。你可以坐公交或打的去城里。所有人都是这么办的,她说着,将票递给了他。 外面很冷,但车里却又太热。车已满满当当,暖气调到最高,空气沉闷而又浑浊。大多数乘客都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吵吵嚷嚷,邋里邋遢。司机骄傲地放起了古斯勒琴曲盒带。斯特凡戴上耳机,调高随身听音量。 他离开萨拉热窝已整整十载。一九九二年三月,就在路障刚刚竖起后不久,父亲将他和母亲送往贝尔格莱德祖母家。待到形势平静后再回来,父亲说。头一两个月,他们巴望着回到萨拉热窝。随后,连续数月,他们又期待着父亲到贝尔格莱德来团聚。他们的等待毫无结果。桥。边界。他不敢肯定,但总觉得十年前正是通过同样的桥出来的。那时,没有边防哨兵。也没有人会叫他出示证件。 桥的那边,一切看似不同。波斯尼亚。狭窄的街衢,焚毁的房屋,幽暗的林子,粗糙的景色。这个名叫符拉森尼卡的小镇单调乏味,一生中,他还从未见过一个地方比它更令人沮丧的了。一过符拉森尼卡就是罗马尼加。他已觉得有点耳朵疼,于是,便摘下耳机。车上一片寂静。谁也不再说话。 这时,道路转弯,朝山下延伸。他们在帕雷车站稍事停歇。他感到胸腔发紧。卢加维卡已近在咫尺,显然。一块路牌上写道: 您正离开斯尔皮斯卡共和国——祝您旅途愉快! 已是黄昏。巴士驶入一座隧道。过了隧道,他开始寻找罗马尼加林子,但林子已不见踪影。下面就是萨拉热窝。接着,这里就是萨拉热窝,真真切切的萨拉热窝。梦中的景象:红色的屋顶,紫色的日落,白色的光塔。他朝司机喊道:“我可以在这里下车吗?”巴士停住。他下车。我正在比斯特里克上面,他想;我正在比斯特里克上面。他缓步朝山下走去。没有什么车辆,除了一些的士。他取出一支烟,点上。我还从未在萨拉热窝抽过烟,他想。 夜色同他一起降临城市。他发现自己站在比斯特里克教堂前。这座教堂正面的色彩,过去曾令他无比喜爱。萨拉热窝足球队服的颜色同它相似。时光回溯,在小学时,斯特凡曾是他们的球迷。 他的双腿拽着他来到帕帕加热卡。三楼一扇窗户里,他的房间的窗户里,一道光隐约可见。一盏灯开着。他看到一个人影:某人正离开床,朝桌子走去。在一部惊悚电影里,他想,此刻,他将看到自己的面孔。所有亲戚都试图说服母亲向政府提出要求,归还他们的家庭寓所,但她不想听。这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他们说。它是你的,他们说。收回来,再将它出手,他们说。一套位于市中心的寓所!他们说。把这钱拿到手,为了孩子,他们说。母亲通常一声不语,不说自己怎么想。只有一回,她开口说:“去他妈的寓所。他们夺走了我的丈夫。” 他不会忘记。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母亲的哭泣将他惊醒。杜尔德死了,她在泪水中一遍遍地说道,杜尔德死了。 他们将他带走了,这就是邻居所说的一切。菲卡娜。她刚从萨拉热窝抵达德国,便打来电话。一天,他们将他带去挖战壕,他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就有人搬进他们的寓所。她这么说。 祖母依然希望他还活着,斯特凡依然希望他还活着,唯有母亲一个劲地哭泣。之后数月,故事渐渐变得清晰。一队士兵将杜尔德,斯特凡的父亲,带走了。菲卡娜说是去挖战壕,但母亲,在近乎歇斯底里的抽泣中,翻来覆去地说,他们将他带去屠杀,屠杀。 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名字留在失踪人员名单上。母亲似乎已甘心接受这一现实。不久之前,有一次,她对他讲述了他们俩前往斯科普里旅行的情形。斯特凡那时还没出生。在塞尔维亚某处路边,她记得,他们看到了不少石头。杜尔德告诉我,她说,这些是家人为在国外牺牲的士兵竖立的路边墓碑,纪念物。我的杜尔德不是士兵,但我也想为他堆上一块。她这么说。 有段时间,斯特凡恨萨拉热窝。他狂热地恨它,一如他在童年狂热地爱它,一如他在成为难民的头八个月狂热地想它。他不恨穆族人。他无法恨他们——足球运动员胡斯雷夫·穆塞米奇和萨菲特·苏斯奇是他的偶像。他只是恨萨拉热窝。他不恨足球队,不恨他的学校和朋友,不恨他的记忆,也不恨他在那里度过的近十二年岁月。他仅仅恨这座城市。让一切夷为平地,他想。让整个萨拉热窝熊熊燃烧。然而,那种恨并未持续多久。于他而言,就连想到萨拉热窝都会感到痛苦。他对自己说,我不会再想萨拉热窝。可是,那座城市总会回到他的脑海,一次又一次,但他竭力抵制,断然接受,这些念头渐渐消失。他专注于象棋,专注于数学,最后,同样专注于米丽卡。随后,母亲交上了移民好运,获得了美国绿卡。他还不到二十一岁,有权跟随母亲一道前往美国。都是因为那首歌。否则,他也不会来到这里。他也不会对母亲撒谎。他完全可以告诉她:我将去告别那座城市。但他几乎都没有力量对自己承认,他的梦依然扎根于萨拉热窝。在这些梦里,他看见他的贝尔格莱德朋友,那些贝尔格莱德街衢,以及那个在贝尔格莱德长大的男孩——也就是他自己,如今的斯特凡。还有米丽卡。可背景却始终是萨拉热窝。他又怎么去告诉她:都是因为那首歌……三个月前,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它。头一次——他可以发誓他是头一次听到它。他从来都不是摇滚歌迷;他喜欢的是高技术音乐。纯属偶然,他在收音机里发现了它。他随即便去买了那盒磁带。 那个组合叫爱克维,爱卡特里娜·维丽卡的缩写,一个贝尔格莱德乐队。他们并不是一个萨拉热窝组合,这兴许正是那首歌击中要害的缘由。萨拉热窝,泥沼和雪做成,歌曲唱道。蓦然,一九九二年三月巴士上看到的情形再度在他心里复活。他看见父亲站在月台上,踩在肮脏的雪里,朝妻子和儿子挥手。这时,巴士正在倒着移动。斯特凡朝他挥手,最后一次看见他。子夜时分。斯特凡在马林·德沃尔,正朝波法里奇走去。从那里,他将打上一辆的士,前往卢加维卡。明天早晨,巴士将返回贝尔格莱德。雪开始飘落。擦去我眼上和眉间的霜,歌曲唱道。离开我,歌曲唱道。斯特凡缓步走着,抽着烟,望着几扇亮着灯的窗户。他听见钟声鸣响。让我的眼看看,再一次让我的耳听听,就这最后一次萨拉热窝作者介绍 穆哈莱姆·巴兹杜尔吉(MuharemBazdulj,—),小说家。出生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特拉夫尼克市。曾在萨拉热窝大学获得过英美研究领域的学位。出版过多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还常常在一些国际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和散文作品。短篇小说集《第二本书》()和《魔力》()曾获奖。 原载于《世界文学》年第5期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zz/8185.html
- 上一篇文章: 创新与魔幻的陷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