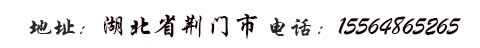悦来文献middot生物艺术与技术
|
中科医院以品质领跑行业 http://m.39.net/disease/a_5882589.html 导读: 生物艺术与技术BioartandTechnology“正如每一种新媒介一样,从广播到视频,从计算机到电信,生物技术的工具和过程为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Kac)以此开启了在《生命迹象:生物艺术与超越》中对生物艺术的开放讨论。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给产业和经济带来了极具潜力的社会效益,在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显然人类也需承受技术所带来的生物问题的威胁。“生物权力(biopower)”和“生物政治(biopolitics)”提醒着我们生物问题不仅限于技术与产业,它们将关联到整个社会和文化模式,同时不断挑战着现有的法治和伦理。当进化以新颖的方式加速展开,进化的尺度将从地质学时间压缩到个体的生命周期。生命形成连续体,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承认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认知连续性,将帮助我们接受、创造新的生命和新的关系,共生和合作的思想在生物技术的时代显得更为重要。“生物艺术是一种致力于探讨生物物质性质的艺术,它操控、修改或改造活体生命和过程。”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Kac)如此定义生物艺术,正表明了艺术家往往是生物技术和相关伦理问题最敏锐的观察者,他们探索了生物技术文化的无数主题和途径,积极塑造话语和公共政策,通过艺术表达激发广泛的辩论。本专题将通过对生物技术文化、生物伦理学、生物学与艺术史的研究,结合大量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实例呈现出生物艺术发展面貌。我们将开放地探讨生物技术的发展,包括生物媒介和生物材料的创新与应用;生物技术在政治与伦理上的交锋,探讨生物主体性和政治媒介的构建;分析包括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Kac)、乔治·格塞特(GeorgeGessert)、奥伦·卡茨(OronCatts)、艾奥纳特·祖尔(IonatZurr)等众多艺术家,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动植物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做出的广泛而先锋的艺术探索。我们的梳理将从上世纪生物中心构成主义的探索延伸到当下的遗传艺术视角,在生物史和艺术史的融合下,同时提供回顾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视角。伯纳德·安德鲁:具身化“奇美拉”——生物技术与主体性文/伯纳德·安德鲁(BernardAndrieu)译/富裕Chacundeuxportaitsursondosunee′normeChime`re’[他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嵌合体]。——波德莱尔,《巴黎的脾脏》,分册。六图1奇美拉,图片来源于网络直到十七世纪末,奇大怪异的身体都有神话的功能:作为神愤怒的标志,怪物(开普勒,)并不像俄狄浦斯难看的脚或命运那般畸形,它作为一个巨大的生物,其肉体被赋予了卓越的力量。然而,我们必须区分神话怪物和生物怪物,前者的肉体杂交仍然是怪诞且自相矛盾的,后者的研究早在希波克拉底的《生成论,X-I(Generation,X-I》和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生成(theGenerationofAnimals)》第四册中就被涉及到。希腊神话中也包含了神话怪兽,人的身体与动物的属性重新组合,被附上如翅膀、蛇和野猪的獠牙,如斯特诺和欧律阿勒(由于美杜莎的嫉妒而被雅典娜改造的角色),以及美杜莎——波塞冬的那怀上他孩子的情人也被雅典娜改造。失去或毁坏其人类的身体决定了这个神话怪物堕落的属性。另一方面,奇美拉生来就具有三重动物的身体,一只在一个身体以各种形式里结合了多头野兽的生物(柏拉图,《理想国》,第九章):狮头羊身龙尾。然而,这种特定的统一性并没有得到维持,就像地狱犬(Cerberus)的化身那样,它有三个头和一条蛇的尾巴(图2)。当嵌合体呈现三个并置的物种时,地狱三头犬则仍然保持狗的形态。奇美拉是一种邪恶的生物,它的近亲是艾奇德娜(Echidna)(半蛇半女)、革律翁(Geryon)三身巨人、美杜莎(蛇发石眼)、斯库拉(Scylla)(她有六对爪、嘴和头,且会狮吼),和被赋予少女的头和乳房、狮爪、犬身、龙尾的斯芬克斯。图2米尔顿-黑山,地狱犬,年。四黑喷墨打印在阿克塞斯纸上,16.3×1.16.3英寸(41.5×41.5厘米),第10版。米尔顿-黑山。由TepperTakayamaFineArts提供。柏勒洛丰(Bellerophon)作为王后斯忒涅玻亚(Stheneboea)的潜在情人,在她遭受国王冷落时被暴露出来。国王于是命令他将奇美拉这怪异的生物赶出国境。根据荷马的说法(《伊利亚特》第六章),他是由畸形的巨人提丰和长着毒蛇身体的仙女艾奇德娜所生的狮头羊身龙尾的怪物。王后对柏勒洛丰产生的通奸欲望违反了待客的法则,在她眼里,柏勒洛丰因其坏品位而拒绝了她。王后因这情欲对象的拒绝感到震惊。在柏勒洛丰与奇美拉不可能的身体对抗中,所有人都认为他的死亡将是肯定的,但这个神话生物给了他一个试炼的机会。柏勒洛丰是波塞冬和伊菲拉女王的孩子;他的名字归功于他谋杀了贝勒罗斯,并解放了被这位科林斯暴君奴役的城镇。在雅典娜女神的帮助下,他成功地驯服了飞马珀伽索斯。然后,他将目标锁定在怪物身上,一个俯冲:奇美拉喷出火焰进行防御,但柏勒洛丰用一个在高温下融化的铅球封住了它的嘴,并把它扼杀了。诚然,奇美拉可被看作独角兽对立面的替罪羊,而独角兽在中世纪是纯洁和贞洁的象征。然而,独角兽是一种神话般的动物,其身体的一致性使是其魅力所在,马的身体与长着独角的鹿的隔离并不遥远。奇美拉是物种的混合嵌合体——狮子、山羊和龙,它通过生产一种矛盾的存在而颠覆了自然秩序。它不是身体的内部蜕变,而是一个复合体。它不是对肉体形式的诋毁,而是通过它的存在,对肉体身份的构成和起源进行审问。这个嵌合体并不像骡子那样是驴子和母马杂交的产物。在将奇美拉赶出科林斯的过程中,半神的神话身体通过对火的掌握战胜了奇异的身体。就艾奇德娜可能是提丰的妹妹而言,性是奇美拉奇异身体的核心所在。半神的身体(必须说是由宙斯的女儿雅典娜赋予的,胜利的提丰在被众神之王毁灭前曾捆绑起她的四肢)拒绝通奸,并杀死了乱伦而生的奇美拉。道德最终没有受到玷污,但范式已经确定。正如弗朗索瓦兹·杜维格诺(Fran?oiseDuvignaud)强调的那样:“野兽总是躺在附近,提醒人们长久以来的秩序。见证了怪物中的怪物——提丰,盖亚无奈地召唤他,作为其精神堕落前的最后尝试。宙斯是个聪明人,他最终消灭了提丰,但在那之前他已经与艾奇德娜交媾,生下了后代,这个后代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的祸害。奇美拉、斯芬克斯、美杜莎和斯库拉”(杜维格诺,21)。通过采用宙斯赋予的这一技术,尘世有望对嵌合体的不纯和恶性进行控制,复合的身体不能持续或繁殖,不仅因为其乱伦的起源,同时因其混杂的构成。图3杰夫罗伊·圣希莱尔(GeoffroySaint-Hilaire)图片来源于网络根据科学史学家让-路易·菲舍尔(Jean-LouisFischer)的说法,迟至“年,杰夫罗伊·圣希莱尔(GeoffroySaint-Hilaire)(图3)才将这怪物般的科学命名为畸形学。作为科学的对象,怪物成为胚胎学领域以及进化论之前的转化主义理论映射的对比对象”(菲舍尔,38)。胜利的柏勒洛丰很快就不再被定义为奇才;将嵌合体的研究置于技术统治的核心,没有这种技术统治,人类就不能同行于神。嵌合体是一个试验,让人类开始接触创造的黑暗面:在这里没有异常就没有创造,没有怪物就没有生物,没有混合体就没有完整的身体。嵌合的身体提出了身份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拥有狮子、羊、和龙的身体?鹰身女妖,部分是女人,部分是鸟(图4)。怪物所指为它身体上的缺陷,也就是说,它把我们送回了自然的畸形。图4米尔顿-黑山,哈比,年。四色喷墨打印在Arches纸上,16.3×1.16.3英寸(41.5×41.5厘米),10版。8米尔顿-黑山。TepperTakayamaFineArts提供。从神话的奇美拉到科学的嵌合体在科学上,嵌合体是由两种来自不同基因、源自两个不同的子宫的细胞组成的有机体。自然界不需要人类干预也会产生一些嵌合体。植物嵌合体是由具有不同基因结构的联锁组织构成的,如苹果树、枫树或虎尾兰(一种与龙舌兰相关的物种)。人类嵌合体是染色体异常的结果:因此,异卵双胞胎,其兄弟姐妹通常是死胎,被输进了后者的造血组织(骨髓),以这种方式怀有两个来自不同群体的血液。所以,人类嵌合体不是普罗米修斯、浮士德或弗兰肯斯坦的中间体。生物科学与人体属性的假想关系在改造的身体上投下了邪恶的阴影。科学可能已经把它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因为它更偏爱于使基因不朽而不是关心人类的境况。与奇美拉的身体不同,转变并不支持双重的生物形式,即使英雄的灵魂被诅咒:普罗米修斯被他的过错所啃噬,浮士德被出卖给了魔鬼,弗兰肯斯坦则被他的出身所困扰,它也只是改变了肉体的形式。转变并不是心灵的改变,而是一种使灵魂能够永远远离洞穴中的阴影,能够遵循辩证法上升到真理的阶段的转化。与嵌合体相比,经改造的身体声称已经摆脱了相异性,然而嵌合仍然在其内部,使其具有身份。转变是一个失败的嵌合体,嵌合体在一个唯一的双重身体中维护着同一性和他者,因为嵌合体是双倍的—不是杰克尔医生和海德先生,而是一个具易识别性的双重身份生物体,并且在人格分裂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必要的身份交替。杰奎琳·卡罗伊(JacquelineCarroy)(年)阐明了人格分裂的神话与科学和神秘主义分裂所共有的许多历史亲缘关系,这在19世纪末激励了许多科学家。奥利维尔·普尔奎(OlivierPourquie’)在介绍妮可·勒杜阿林(NicoleLeDouarin)的工作时表示:生物嵌合体的基础建立在“相似领域的替代”,而不是互补身份的相似上。嵌合体包含鹌鹑细胞和鸡细胞;“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胚胎嵌合体发育正常,通过费尔根·罗森贝克(Feulgen-Rosszenbeck)的核着色”(普尔奎,42),可以识别构成神经管的鹌鹑细胞以及从神经褶皱迁移出来的神经脊的衍生物。无论细胞的分化状态如何,都可以识别出移植后的细胞。嵌合体的融合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在同一体内保持着不同。我们需要跟踪不同者在一个单元内的迁移,而后者不会消失:每一个都是另一个的提示。然而,嵌合体的模型属于当代幻想,即发育生物学的幻想。温克勒在年创造了第一个植物嵌合体:这些异体移植由来自两个不同物种的成对细胞组成,它们各自的遗传潜力没有被改变。只要不对生殖细胞做手脚,嵌合体就不能传播其体征状态。嵌合体的移植身体在二十世纪初,嵌合体的科学模型显示,移植的身体是现代主体性的代表。通过移植,主体在赋予技术一个身份的同时也能够使构建身体成为可能。当马修·雅布莱(MathieuJaboulay,-)和亚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Carrel,-)分别于年和年尝试首次移植时,嵌合生物学诞生了。对于任何接受移植的病人来说,仍然存在着嵌合体的耐受性问题。在这方面,克里斯蒂安·卡布罗尔(ChristianCabrol)预言说:到年,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这种耐受性,在移植后,接受器官能接受两种器官,即自己的和移植的器官,就很好了。而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嵌合体!——确实!在古希腊,嵌合体是一种表现出不同物种特征的神话动物,例如,半人马的身体上有一个人类躯干(图5)。了解耐受机制将是实现移植完全成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突破,使宿主避免了免疫抑制治疗的缺点和慢性排斥反应导致移植的逐步摧毁的倾向。(卡布罗尔,)图5米尔顿-黑山,《半人马》,年。QuadBlack喷墨打印在Arches纸上,16.3×16.3英寸(41.5×41.5厘米),10版。8米尔顿-黑山。由TepperTakayamaFineArts提供。宿主必须将"他者"纳入自己的身份,以便继续生存。他从未完全成为一个“奇美拉”,正因为有一个能使身体本身接受相异器官的技术贡献。这种技术贡献使移植的器官处于机械身体的结构内。正如身体社会学家大卫·勒布雷顿(DavidLeBreton)所指明的:“当象征主义抛弃身体的时候,那么,后者确实只剩下一套驱动,即一个可交换功能的技术组织”(勒布雷顿,-)。如果身体的这种客体化确实在结束基督教的化身身体方面有一定的作用,那么它也指出了主体与生命物质的一种新关系。身体的变形定义了一种主观的、不再是形而上学的化身模式:现在主体通过身体定义为一个由各种元素嫁接而成的复杂网络,即可超越他的身体。在生物学家和哲学家米歇尔·蒂邦·科尼略特(MichelTibon-Cornillot)的眼中,嵌合体动物、植物或细菌预示着一种新的生物性质的工程,在其中,人们可以重新解读一种目的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目的已经取代了被小心翼翼地从世界上驱逐的旧有的意愿。这些新生命的出现,转基因和嵌合体,被设置在如此激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它们的存在真的不会构成问题。(蒂邦·科尼略特,)尽管如此,这些新的"理性的假想"物体并不是虚构的物体。它们属于自然界所允许的生物兼容性,即使不是由自然界本身在其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即使嵌合体主要是科学的产物,它们也源于人类对生命机制的理解。这种生产的合法性不应受到质疑。像哲学家马克斯·马库齐(MaxMarcuzzi)一样,人们当然可以在生产中看到"人造身体",并断言:畸形学是最广泛形式的生物学,也是最严格的本体论形式;但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绝对的参照或协调,无论是神授的还是自然的,可以作为一个客观和恒定的规范,除了个人,没有其他规范可以决定什么是或不是畸形,从而也决定什么组成身体,以及身体可以有什么形式。(马库齐,-)然而,染色体畸变及异常则在生命物质的一个基本层面。生命科学一直在研究这些反常模式,以便通过经验和实验的双向镜子了解自然之镜的反向效应。使嵌合体成为热点的不是时尚,而是一个新世界的定义,自然人以物质的本质胁迫身体,又用假肢和移植物来使它达到适合的状态。转基因嵌合体和生物权力生物技术的使用助长了对未被阉割的身体幻想,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既是此又是彼、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身体。社会学家帕特里克·鲍德里(PatrickBaudry)把对废除所有限制的渴望理解为"身体极限"(鲍德里,),因为跨过这些限制就必然会导致身体的消亡。然而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与自我的极限关系是通过突变来实现的。自由主义和生物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结合所引发的个人身体的使用,使我们的时代主体不仅能够改变总体形势,而且能够改变个体的身体本质。图6《人耳鼠(Earmouse)》(),来自CharlesVacanti(查尔斯·瓦康提)、JosephP.Vacanti(约瑟夫·瓦康提)(美国),曹谊林(中国)(麻省理工、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图片来源于网络可以肯定的是,出于一些对遗传基因的道德和欺诈问题的考虑,一些国家的生物伦理法现在确实禁止“转基因人类”,但这能持续多久?所有的体外干预只应创造拼接式的嵌合体,以便通过对体细胞的治疗性改造确保生命延续,而不对生殖细胞进行明确的干预。积极的优生主义因此被禁止,人类转基因嵌合体回到了文学对象的位置;然而消极的优生主义确实围绕着我们:任何人都会承认,在选择用于体外受精的胚胎时,消除遗传性疾病,以避免必须的人工流产或不得不抚养严重残障的孩子,是非常方便的。畸形从一开始就被消除了,从而通过净化遗传物质量重新组成了人类嵌合体。在我们的世纪之初,转变成为了一种改变外表的模式和时尚,常常与存在的改变混为一谈。常理取得了胜利,但与人体相关的类比仍然占主导地位。通过开放所有的可能性,人们确实在不提出关于实施转基因的基本问题的情况下放宽了存在的概念。抛弃人体与其说是一种狂喜,不如说是与自己最初的遗传基因的最终决裂。结束基因身份所强加的阉割愿望,难道不是对自身物种自我厌恶的承认,或者是我们忘记了对切尔诺贝利或广岛的孩子所造成的基因突变的证据?最终,当人类像动物和植物一样,以转基因的神话取代了创世纪和堕落的神话时,人体将成为一个基因嵌合体。阿尔道夫·赫胥黎(AldovsHuxley)在他年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年的第二篇序言中用以下术语描述了这场革命:“将要发生的真正的革命不是发生在外部世界,而是发生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中”(赫胥黎,12)。个人的肉体变化已经不够了,物种的变化将有序的来到。如果十八世纪是异装癖的世纪,十九世纪末是雌雄同体的世纪,正如米歇尔·福柯年所说,我们仍然需要了解嵌合体这个主题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传播中预示着什么。在福柯所描述的条件下,人类嵌合体不会将其性别的选择权留给个人。这将是生物权力在性和真理之间建立的意识形态链的合理结果:拥有一个真正的性别并不被人类嵌合体理解为从社会性别退回到生物性别。真理通过将两种性别合二为一而达到其生物学上的巅峰,双性被纳入一个单一的遗传单位。在成为转基因人之后,人类不会再有更多选择:科学将决定身体的有效性,健康或经济将再次被用作托辞。通过对转基因的承诺,转基因研究已经成为法国国家级优先事项,这就意味着要回到福柯最初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性别吗?(福柯[],bk.IV,)。嵌合体可能是一个真实性别的最后的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技术工程,通过造物的完整性最终提供了对阉割的否定。赋予每个人自己的嵌合体身体已经成为身份的标志,而它曾经只是一种社会外观和表面的模式(勒·布雷顿(LeBreton))。外表是外在的,具身性是内在的。对二元论的拒绝与其说是希望告别自然的身体,不如说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体。通过他自己的身体,主体可以塑造形式,但也可以塑造物质本身:对身体的标记是身体主体化的第一种模式,而基因操作提供了一个塑造人性物质的可能性。身份认同正在通过技术手段构建自身的文化形式。身体崇拜不仅延展了自我自由,它也成就了自我培养和自我文化。如果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更新身体的商品化,在身体的无限分割中继续维持主体性,消费者就会在这循环中被诱惑去消费自我。图7艺术作品:《年轻的家庭(Theyoungfamily)》(),PatriciaPiccinini(帕翠西娅·皮奇尼尼),图片来源于艺术家网站在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我们乐于见到一个人的身体属于他个人。这种享乐主义的消费主义满足了人类的身体,也导致了过度肥胖和高风险行为。一旦身体成为它自己,个人也可以通过将其个性化而不是退缩到个人主义中来使它成为主体。当主体化试图将主体化身为身体本身时,肉体的装饰将作为表达模式。存在不是一种本质,它要么是外部的,要么是超越主体的。萨特设法将人类的本质还原为存在。我存在,即是我的行为。存在主义要在女权主义和世俗的体现中找到特权的模式。性别和他们的化身模式把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引向了承认肉体存在的身份斗争。肉体的构建通过身份强化和文化升华来直接转化为一个人的存在。身体崇拜已经被其文化和教化所取代,后者在主体中创造了他们的肉体价值:定位了他或她的性别和性征,他或她的行动,他或她的基因或大脑。身体解放导致了对嵌合体化身的强烈渴望。通过使用生物学和现象学,我主体化身或具身化思想的概念与弗朗西斯·瓦雷拉所创的工作相似。通过提出用“活的身体”解释认知的建议开始,到化身(或具身)的概念不再具有基督教传统的二元论意义。精神(思想)现在通过产生它的身体而存在。按照瓦雷拉的说法,现在应该达成一个调解,既不把认知作为一个预设的外部世界的重构(现实主义),也不作为一个预设的内部世界的投射(唯心主义)来研究,而是作为具身化的行动:“通过使用‘具身’这个术语,意味着我们强调两点:第一,认知依赖于具有各种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所带来的体验,第二,这些独立的感觉运动能力本身被包含到到一个更广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语境中”(瓦雷拉,辛普森,和罗夏[],)。让我们找到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长期寻找的生物学和现象学之间的联系:“行动表明认知结构是如何从不断重现的感觉运动策略中产生的,从而通过感知指导行动。主体性生物技术现象学不是一门统一的新科学,而是一种交叉理解: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人体化的身体。一个生物技术现象学的主体对嵌合体身体的渴望现在只受限于生物技术的幻想。决定实现一个完全的生物人工的身体可能不符合生物伦理规范和法律,即忘记了医疗技术进步所确保的生物主体性。个人利益中,一个人援引他在一个有尊严的身体中生活的权利,将使人工生命的研究合法化。假设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我们的身体:这是否足以废除这种客体/主体关系,以充分体现主体?因为身体可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具有这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任何内容都无法分解它。通过改变他或她的身体并使其尽可能地接近本人的意愿,生物技术的存在实际上将改变生物时间,不是停止或延长它,而是作为生物主体性运动强烈地存在于我们的生物时间中。通过塑造他或她身体的物质,主体不仅形成了他或她自己,主体还获得了关于他或她肉体运动的信息。通过改变身体,主体发现自己是在运动。与其说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或审美理想而建构他或她自己,其实在极端情况下,运动的主体希望无休止地修改他或她自己。鉴于身体不再是自然的,或者至少身体的个人及社会表现将其定义为完全文化的和技术的,我们就可以无休止地解构和重构身体。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可以被替换,就像生物技术的组合玩具中的零件。然而,活体的机械化必须在其人造性中具有功能,就像让·吕克·南希年写作的关于他移植手术的文章《入侵者(TheIntruder)》中所写。我们对主体性的精神依恋使我们保持在自我统一的想象中,身体本身产生的精神是独立于生物状态的幻觉。众所周知,我们被赋予的身体会被磨损,会生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会因为时间而衰老。通过改变身体,我们可以阻止这种生物的时限性,或者通过减缓衰老过程,或者通过身体空间性的更新来弥补时间的问题。总结通过在人类物种内部创造新的物种,生物选择的个体,如年出生的婴儿亚当,通过基因筛查和选择以拯救他生病的姊妹,这表明现在使用生物技术改变身体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可行的。这里仍然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托辞。这些变化不仅意味着生物方面的后果,同样意味着社会方面的后果。现在,基因组科学赋予了家庭关系、性行为和与自身身体关系变化的合法性。作者伯纳德·安德鲁(BernardAndrieu)法国哲学家、身体历史学家,法国南锡大学教授。他的哲学写作专注于神经科学与身心问题,以及晒黑、触摸、露天和沉浸等身体实践的历史。译者富裕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生物艺术与科技研究硕士在读,本科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视觉传达方向。专注于艺术与科技话题研究和生物艺术实践,作品曾入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实验艺术展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合成生命与生态本科课程助教。参考文献1.Baudry,P.Lecorpsextre?me:Approchesociologiquedesconduitesa`risques.Paris:L’Harmattan,.2.Cabrol,C.Ledondesoi.Paris:Hachette/Carre`re,.3.Carroy,J.Lespersonnalite′sdoublesetmultiples(Entrescienceetfiction).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4.Chatelet,N.Late?teenbas.Paris:Grasset,.5.Duvignaud,F.Lecorpsdel’effroi.Paris:LeSy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zz/7867.html
- 上一篇文章: 母亲节品赏中外名家画笔下的母亲
- 下一篇文章: 陈柱传闻与想象清朝对布鲁特的早期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