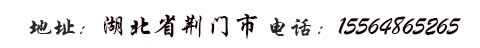看,这里是亚欧大草原的尽头
|
看,这里是亚欧大草原的尽头 ——在牧人和农夫的边界上 一、大草原的尽头 车凌敦多布告诉我,他意外地看到了一首关于夏日塔拉的歌谣,这是阿努达喇翻译整理的19世纪俄罗斯的卡尔梅克蒙古喇嘛巴赞的游记时发现的。巴赞喇嘛从伏尔加河动身,通过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穿过祁连山,前往拉萨朝圣,在翻越祁连山途中路过夏日塔拉有感写下了一段关于夏日塔拉的文字。巴赞喇嘛返回故伏尔加河故地是从海路走的。在旅途漫长的时光里,他们常常即兴编歌谣来歌唱。这也是游牧人的习性。 阿努达喇将巴赞喇嘛的托忒蒙古文游记中的那首关于夏日塔拉的歌谣译成了汉文,歌词大意如下: 从伏尔加河到祁连山/草原连绵不断/有人指着雪山下这片金色草地说/ 看,这亚欧大草原的尽头——夏日塔拉 夏日浩特古城长满了芨芨草/黄羊在那里奔跑/我的眼泪滴在了斡尔朵河边/ 看,这亚欧大草原的尽头——夏日塔拉 天边那一列高峰就是边界/翻过那里就是种地的人们/秋风吹拂着我们的驼队/ 看,这亚欧大草原的尽头——夏日塔拉 在这首歌谣中,亚欧大草原也称之为“额客·瑙套格”。奇妙的是,这首歌里说得也是车凌敦多布披肝沥胆地讲了许多年的话——给这些大草原尽头的牧人。 几年过去了,那是年夏天的一天,在车凌敦多布的夏日塔拉小屋。他的对面坐着的是西斌、杰奇和我。 “……你们知道吗?我为什么重返夏日塔拉长住?因为我病了,30多年前我遇到一个永昌县农村的中医奇人,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生研究匈奴历史、星象和占卜。他说我也许患有一种罕见的思乡病,也许是古代的某个匈奴单于魂附体。 呵呵呵……如果是英雄远祖之魂附我身体,我幸运之至。我姑且把这种病叫做‘亚欧大草原综合症’吧。这个像巫师一样的老中医说我这个病根,也许源于数百年前还完整的亚欧大草原。他还对我说‘大草原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你如今也许只有绝地逃亡,再也不要去想不要说不要写也不要歌唱那个亚欧大草原……仲夏月圆之夜,到旷野或山岭间用心倾听杜鹃的歌声,但是要避开月亮之母——猫头鹰的笑声,还要远远避开朝你嗥叫的白狼……你知道吗?你们尧熬尔人和你们的远祖匈奴人一样——遇到白狼朝你嗥叫必死无异。’老中医说得玄而又玄,而我则听得绕有趣味。” 车凌敦多布一边笑一边对我们说着,我们都笑了。我心里想,这么说,他提到的巴赞喇嘛似乎也患有“亚欧大草原的综合症”,还有许多人都患有这个“病”…… “你们放牧的这个夏日塔拉就是亚欧大草原东南边缘的尽头……从这一头一直向西就可以到达这片大草原极西边的尽头——伏尔加河和多瑙河……这片横亘欧亚大陆中心的亚欧大草原,就是我们的先辈尧熬尔人叫做额客·瑙套格的地方,也就是传说中那匹苍毛苍鬃的大公狼带领我们的可汗、牧人和马群走过去的大地,所以也叫做‘布尔蒂赤纳·瑙套格’——苍狼大地。 从我们脚下的夏日塔拉往东翻过那几座山,或是顺着斡尔朵河走出峡谷就是河西走廊农耕地区——属于东亚农耕地区,也就是中原农耕地区的延伸……” 车凌敦多布说到这里结束了话题。我心里想,如果那个中医说他有病,那么他的病根本没有痊愈,因为他还在不断地说亚欧大草原说匈奴说杜鹃猫头鹰白狼…… 千真万确的是,车凌敦多布在夏日塔拉美不胜收的夏营地和冬营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中年以后又和妻子回到夏日塔拉长住。 这个亚欧大草原东南的尽头夏日塔拉——祁连山北麓雪山下的小镇上,有几种亚洲居民,汉人——主要来自武威、永昌、张掖和山丹一带。尧熬尔人——使用突厥语和蒙古语。吐伯特人——使用安多华锐方言。少量的回民——来自青海东部或甘肃临夏。还有极少的蒙古人——卫拉特部和喀尔喀部的居民。还有更少的土族和东乡人。南边的皑皑雪山和熠熠闪烁的牧人之星在天空下审视着一切。 夏日塔拉的北境主要由马营三个村的尧熬尔人和原泱翔的吐伯特人放牧。 ~年甘青边界的大搬迁,尧熬尔几个部落来到夏日塔拉,他们和天祝县泱翔和铧尖二地的吐伯特人在行政区域上划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肃南县),在夏日塔拉成立了一个区公署,区公署下辖他们几个民族或部落组成的几个公社,公社以下是生产队。 车凌敦多布叙述了他和阿努达喇巡游夏日塔拉北境——泱翔的一个古隘口和马营三个村的经历。 二、夏日塔拉的北境 年夏天,车凌敦多布和阿努达喇绕着夏日塔拉北境——夏日塔拉北部边界走了一圈,也就是沿祁连山北麓紧临河西走廊平原的山地草原。 他們乘镇上的汽车过斡尔朵河大桥,从夏日浩特——黄城儿古城(后来改为皇城)和水库旁边绕过。这条河和古城都在巴赞喇嘛的即兴歌谣中一唱三叹地说到了,也在诸如《永昌县志》《凉州府志》《蒙古佛教史》《安多政教史》《秦边纪略》《阿勒坦汗传》等等各种史料中不断提到。 穿过水库边的隧道顺斡尔朵河向北,走三十多公里的峡谷先到泱翔盆地。如果顺着峡谷再往北,就可以出祁连山到河西走廊农耕地区。泱翔盆地是吐伯特农牧民聚集地,古老的佛寺沙沟寺就在泱翔。车凌敦多布他们一行在朋友白加央家喝了茶,然后折头往东爬上了东顶高地。东顶高地缺水,但牧草茂盛,是泱翔吐伯特牧民的冬春牧场。从这里他們朝北走,一系列屏障般的山岭耸立在前方,山崖上一个古代隘口藏在高高的芨芨草丛中,碎石沙土中废弃的古道从那里蜿蜒而过。当地人说是1949年前,国民党時期在甘肃和青海的马步芳集团占据夏日塔拉后,曾修建了一条武威市通夏日塔拉的公路,就是从眼前这个古隘口通过,从隘口向北望去,山势依次下降,从隘口一直向北的道路弯弯曲曲地渐次下降伸向平坦的河西走廊,山下就是河西走廊的武威农耕地区。阳光灿烂,风从隘口山崖蹑手蹑脚地吹过。烟雾迷濛的平原上依稀可见汉族村庄、耕地和公路。形形色色的牧人和农民一直不断地争夺的历史如梦幻闪烁。在本地的吐伯特人中传说,很早以前,因为山下川地的农民人多势众,赶着大量的畜群占了这个地方,吐伯特人无法放牧,他们请来法术高明的持密咒者做法镇住了水源,这里成了一片干涸没有水的草地。农民的畜群无法饮水就撤走了。这片山地草原重新被吐伯特牧人放牧。 他们返回小镇后,准备重点去看一下夏日塔拉另一处北境,也是几十年来农牧草原纠纷最多的边界——肃南县和永昌县的界线,具体说来是肃南县的马营三个村和永昌县新城子镇的界线。肃南是祁连山区以尧熬尔人为主的牧业县,永昌县是祁连山下河西地区的汉人农业区。 网上的资料显示,永昌县属金昌市管辖,永昌县新城子镇位于祁连山北麓山下,距永昌县城39公里。新城子镇南邻从事牧业的肃南县夏日塔拉小镇(皇城镇)。新城子镇北部是扇形平原为主要的农业区,西邻山丹军马场。新城子镇总面积.1平方千米,辖13个村,总人口人()。有汉、回、吐伯特、满、蒙古、土等6个民族。 西斌给车凌敦多布和阿努达喇安排了车辆,药罗葛部落杜曼氏族的杜雪峰村长开车。从夏日塔拉小镇启程,沿着马皇公路绕过铁山头,拐弯进入草地牧道到小泉沟,再向西北方向走,牧道的南侧依次是北芨芨沟,煤洞沟,磨石沟,柳洼槽,火松林垭豁。牧道北侧是独山子滩。面孔如刀俏斧砍般粗犷英俊杜雪峰说,独山子滩现在被永昌县新城子镇的农民占据放牧,眼前约有20来群牦牛,四五群羊和一群马分布在山峦间吃草。那里还有以前夏日塔拉的牧民放牧时修建的房屋遗址。如今,这里被永昌人占据已有好多年。 永昌县的草山或戈壁地方早已被国家禁牧,包括紧靠牧业地区的草山。杜雪峰说这些永昌新城子的农民又用国家发放的禁牧补偿款收购了牛羊,赶到这里放牧。这样显然也是违背国家政策的。 最近的草原纠纷是年中国农村和牧区联产承包后陆续发生的。牧道旁边的壕沟年左右肃南县和永昌县的草场纠纷时,夏日塔拉的牧民挖的壕沟式防护围栏,用来阻挡永昌县抢牧的牲畜。后来永昌县的人挖断了壕沟剪了铁丝围栏,赶着畜群到属肃南的草场上放牧。 我们走到了一个积雪覆盖的垭豁,这里叫火松林垭豁。山坡上有一个被毁坏的属于肃南县的水泥石碑,看不出任何字迹。杜雪峰说是永昌县的人砸坏的。雪后的道路泥泞不堪。一个骑摩托的永昌人过垭豁时停了下來,狐疑看著他们。边界上的人是很敏感的。 永昌人问车凌敦多布: “你們在找什么?” 车凌敦多布恶作剧地說: “黃金。” 永昌人有点无奈地冷笑了一下走了。车凌敦多布望着那个人的背影笑了。 不能以对或错,先进或落后来简单评说农耕和游牧,这是基本常识。自从《圣经》旧约中所说的族长时代,农夫该隐杀了牧人亚伯以后,草原牧人和耕地农夫的冲突似乎从来没有停止。地球上,牧业和农业边界,漁猎采集和农耕的边界上,一直沒有中断过各种大大小小的纠结。凡是边界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从来都是多事之地。一切似乎都是人类的宿命。如果真有“亚欧大草原综合症”,那也可能源于上古的族长时代。 三、药罗葛部落的西斌 西斌所属的尧熬尔药罗葛部落的部分牧人,就在夏日塔拉的西北边界,紧靠着永昌县新城子镇。药罗葛部落大约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人采用汉语名字。除个别人以外,如今尧熬尔人大多也都使用着汉语名字。 西斌属药罗葛部落安江氏族。当年车凌敦多布背着一个用红色油漆喷着红五星的黄色帆布书包,离开黑帐篷到夏日塔拉小镇的学校上学时,隐约记得有一天,一个名叫西斌的尧熬尔男孩也来到了学校,那时的西斌一脸的调皮和傲气——坏坏的。西斌后来放过牧也当过兵,再后来当过工人也做过个体生意,中年以后一直当着金子滩村的村长。这个村子叫“金子滩”是因为清代有人在这里挖过沙金,所以叫金子滩。如今的西斌很瘦也很精神,机智而强悍,敢作敢为。他常喝酒,但他喝酒从不误事。开车骑摩托,不知摔伤多少次昏迷多少次,瘦俏的身体浑身都是累累伤疤。他的交游很广,在牧民和农民中,边界的两边城镇、农田和牧场上,黑白两道都有形形色色的朋友和熟人。 有一次他酒后开车,车翻了他也昏迷过去,家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多处骨折,建医院治疗。他妻子和几个人拉着昏医院,他妻子对医生说,“麻烦你们检查一下,如果他的头脑还清楚就不住院了,别的地方骨折了我们把他拉回去家慢慢养好。我们家的羊啦牛啦摔坏腰腿也是这样养好的……” 医生气的骂个不停。 西斌家的冬窝子在公路旁边一个山沟里,一座山环绕着他的房屋和牲畜棚圈。西斌告诉车凌敦多布。西斌的祖父曾长期放马,那时祖父是生产队的老马馆,相马驯马都有超常的本领。他的祖父曾告诉他一件奇事,他的祖父赶着马群去饮水时,马群奔驰着从山梁上走过,每次马群走到一个山冈时,奔驰的马群总是会停在那里,绕着这个小山冈走几圈,然后才缓缓离开。每一次他赶着马群走过那个山冈时,马群总是重复在那里跑着绕一圈并且停留一阵才离开。马群从那里走过时,从来没有一次忽略而过。他祖父在放马时一直留心观察那个山冈,看见那个山冈上空总是有一朵白云停留,那怕是天空万里无云,但那里总会飘着一朵白云。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个山冈总是会有一朵云在飘浮。他祖父非常惊讶,这是个什么样神秘的地方呢?在这里又发生过什么事呢?能量?山神? 车凌敦多布想,这个诡异而美妙的山冈和匈奴时代有什么关系呢? 许多年来,西斌开着他那辆落满尘土的小车飞驰在夏日塔拉的群山草原间,车的后背箱里总是捆放着一只肥大的羯羊,那是用来招待来自四方亲朋好友的。 西斌对车凌敦多布讲了一段夏日塔拉北境边界的事。几十年来的主要矛盾就是因为,永昌县新城子镇农民常把耕畜赶到夏日塔拉的山上放牧而产生的。而牧民不可能把牲畜赶到永昌县的耕地上去放牧。他说夏日塔拉方面是马营三个村牧民七百余人在北境群山中放牧,对方是永昌的六七个村一万七千余人的农业区。 大约是-年的7月1日,西斌骑摩托从镇上到马营,永昌县新城子镇几个村的农民几百人,集中起来翻越火松林垭豁来到西水滩村的小柳沟和大柳沟一带。新城子的农民带头的叫西仁才(译音),他是个大队队长。他带人计划夺取夏日塔拉的沙坝台、南芨芨沟和北芨芨沟。当时沙坝台有煤矿,煤矿利润很好。南芨芨和北芨芨沟草场紧挨新城子地界,草场很好。 西仁才带领的人抢走夏日塔拉牧牧的牛和羊,拉倒黑帐篷,抢走帐篷里的财物,砸坏冬窝子砖房或土屋的门窗。当时西斌到沙坝台,看到有八九个牧人妇女和孩子们逃了出来,哭泣着向他们诉说,有的人家房子被永昌人拆了,有的人家黑帐篷被烧,财物被抢走,有的人家的羊被赶走,人被抓走。就剩下他们几个妇女带着孩子逃了出来。 永昌人来牧场上抢劫时,逃跑的牧民有的背了自己的衣服匆匆逃跑,有一个牧民还背着自己的被子跑。几个人跑到半路累得气都喘不过来,旁边有人指著路旁的一個漆黑的洞说,你把被子扔到这个洞里,永昌人走了后你再来取上。他把被子扔下去时,好半天才听见“咚”的一声,原来是个很深的洞,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来。 这一天,永昌人抓了马营的乡长白文清,副乡长贺建英。那时夏日塔拉的区长蔺长福正好去解手没有被抓,他乘机逃脱。永昌人殴打了两个乡长,还往白文清嘴里喂了马粪。 年秋天,永昌人上千人来到夏日塔拉挖野生柴胡,那一年夏日塔拉草原上生长的野生柴胡很值钱,一根柴胡好几元钱。但是挖柴胡对草原破坏很大。挖柴胡的永昌农民最多时每天约有人左右。 新城子镇的农民向着夏日塔拉蜂涌而来,一部分人乘3辆汽车,另一部分人赶着耕牛和马,着草叉、棒子和石块。他们从马营三个村的夏牧场到冬营地。拆毁铁丝围栏,烧毁牧民的黑帐篷,砸毁冬窝子的砖房和土坏房的门窗,能用的能拿的财物全部抢走。 永昌人在夏日塔拉马营的草地住了一个星期,抢掠、放牧耕畜和挖柴胡等药材。 西斌带了九个人去阻挡挖柴胡的永昌人。他们在白泉垴看到有60个人挖柴胡,他们抓了五六个人,其他人跑了。他们把挖药的人打了一顿,脱了他们有鞋,让他们赤脚回去。西斌等人又从死人沟垴子里翻过去,挖药材的永昌人跑了,他们怀疑某个尧熬尔牧人家里藏了永昌人。 他们踢开那家牧民冬窝子的房门,看见有四个永昌挖药的女子,小伙子们扭着女子的头发从小河水里拖过去打了一顿才放人。正在火头上的小伙子们把那个藏匿永昌人的牧民也打了一顿。西斌说,他看到小伙子们打人很凶,但是看见漂亮的女子他们总是不太愿意打。 械斗中,有人传言说本地牧民在新城子有亲戚关系的常带他们来挖药材,这类人被牧人看不起。马营最北边的牧民和永昌新城子紧紧相邻,牧民常去新城子镇买东西等来往很多,所以有些牧民新城子的农民很多都是熟人,他们不太愿意打新城子来挖药的人。 顾令氏族的一个老母亲前去阻止在草地上挖药的永昌人说: “你们不要再挖了,你们这样挖把我们的草原全毁掉了。” 永昌人对她说: “你们这些黄鞑子(指尧熬尔人)傻着呢,挖上药你病了就得吃药呵!” 夏日塔拉的牧民们急了,一群牧民小伙子抓了20来个挖药的永昌人,他们让永昌人站成两排,互相打耳光。几个妇女吓得把馒头拿上给牧人小伙子们,被小伙子一脚踢得馒头飞上了天。有的永昌人吓得哭了。小伙子们还逼这些永昌人给他们唱歌,把他们的鞋也全部给脱了,抽完他们的摩托的油,只留下了学生和小孩们的鞋。成年人几乎都挨了打才让放他们回去。 公路卡子上,牧民潘抓了一个永昌人,潘的妻子和孩子被永昌人殴打,黑帐篷被烧,财产被抢走。潘正在火头上,他把刀子插到那个永昌人的腿子上又旋转了一圈,旁边看的人吓得尿失禁。 有一天,西斌带着四个人遇到一个新城子小伙子,他们几个人把那个小伙了打了一顿。当时西斌戴了顶白帽子。那个人跑到远处回头叫骂: “肃南县的这几个狗日的,你们等着,我把人领上来把你们做死……” 后来,一个姓吴的新城子人给西斌剪羊毛,说他的姐夫被一个戴白帽子的人打坏了。边界上这种事也是常见,有的农民和牧民互相打过架后,过一段时间还会有来往,有时还会说起打架的往事。 那一年,夏日塔拉几个乡的年轻人都被区上集中起来和永昌人械斗,除了马营还有铧尖、北滩、东滩和泱翔的人。铧尖人在械斗中抢了永昌人的东西,杀了永昌人的耕牛,把牛肉拉上后开车返回铧尖。马营三个村的小伙子们则把永昌人的耕畜黄牛杀了后煮着吃了。 肃南县和永昌县举行了边界谈判。永昌县的县长姓曹,曹县长见到肃南县的人说“你们的人用血写的申请,要求归永昌县管辖。”没有人证明他说得是不是真的。当时在夏日塔拉的牧民中也谣传一部分尧熬尔和吐伯特人要求归金昌市管辖,永昌县也属金昌市管辖。 双方重新确定了边界。以夏日塔拉西北边的马营庙石沟口子,做为肃南县的夏日塔拉和永昌县新城子的界线。谈判后,永昌人开着汽车来退还被抢去的牧民财产,所有被抢的东西都装在一个个蛇皮袋子里。永昌人走了后,夏日塔拉的牧民打开一看,蛇皮袋子里全部塞满了草。 四、海生录的讲述 那天,车凌敦多布他们在火松林的牧道上遇见西水滩村的支部书记海生录,在药罗葛部落里,海生录则属于一个外来的姓氏,他的父亲原来是车凌敦多布所属的鄂金尼部落的绰罗斯氏族,早年流落到了药罗葛部落。 西水滩村名字源于一个名叫柳沟的山里流出的一条小溪,那个小溪周围就叫“西水滩”,所以村名就叫西水滩村。居民仍是药罗葛部的一部分。西水滩村和金子滩村西城村一样,一直在肃南县和永昌县的交界上。 在平缓的火松林山坡下,海生录站在草原道路旁边讲起了他們家三代人和永昌人争夺草场的经历。 海生录说他們从记事起就和永昌农业区的人争夺草场。他小时候,永昌新城子的农民把马群赶过来在牧民的草地上抢放,海生录们奋力阻挡马群,去打人或被打。他说现在一看见马就想起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他的爷爷当了三年队长,父亲也当了30年队长,他也当了30年村长。海生录讲述时,饱经风霜和忧患的神情中,有一种长期在群山中独当一面的人才有的特点,还有一种创伤、无奈和孤独。这也是边界地区或草原尽头的牧民所特有的。 他说他小时候遇到永昌新城子的人来抢劫,几次抢财物抢牲畜。他们一家三代人就在这个草原和农耕边界上打架争夺草场。他记得清晰,永昌的农民把绳索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拉到山下殴打。他父亲是个小个子,嘴硬不认输,永昌人打他的耳光,一边打一边骂: “看你个子小小的,嘴还犟的很”。 海生录当村长时,指挥牧民宰羊煮肉,宴请新城子的大队书记和村干部们,请求他们不要让农民到牧场上抢劫或抢牧。 年夏天,永昌县新城子的南湾、赵丁庄、塔尔湾和刘克庄四个大队多人上山来抢劫和抢牧,海生录所在的西水滩村牧民有28户被抢劫。海生录当时回到家时,家没有了,黑帐篷被拉倒,帐篷里的锅啦案板啦都扔在一边,家里老人、妻子和孩子全都跑得不见影子。在冬窝子被毁坏的墙上写着“活捉海生录”“剥掉海生录的皮,抽掉海生录的筋”“还我草原”。海生录是村长,永昌县新城子有很多人都认识他。 五,盖嶂大坂 杜雪峰开着车,他们到了永昌县和肃南县之间的盖嶂达坂(也叫杆杖达坂),盖嶂达坂是祁连山北边的一个支脉。“盖嶂达坂”这个名字的来历谁也說不清,地方志上也沒有记载。车凌敦多布小时候放牧时,从铁奇沟冬窝子的山梁上常常眺望这个远看是褐色的高山,那时候看起来盖嶂达坂高耸入云,无法逾越。寒冷的冬日,黄草漫漫的山峦,咸味的水和从远处驮来的冰块几乎是那个时候的主要记忆。 车停在了盖嶂达坂山下的鄂博梁,所谓鄂博梁是因为那里有古代居民堆起的石堆,如果按藏蒙佛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古时候的石堆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鄂博。整个祁连山地区和吐伯特高原随处可见这种古迹。一般认为是用来镇邪压魔的。 站在盖嶂达坂下的山坡上南望祁连山主脉,眼前还是一片绵延起伏的黃草地,洒满阳光的群山和草地。西南边积雪覆盖的黑色山脉是巴颜哈喇,远处东南边白雪皚皚的雪山是百花嶂,祁连山主脉上空的蔚蓝天空上飄浮著朵朵冷云。神峰阿米冈克尔是匈奴人的圣地,矗立在甘肃和青海交界上。祁连山的这一段在新地图上标为“冷龙岭”。 脚下有一条新修的牧道或简易公路,杜雪峰说是村长西斌带人修建的。深秋金黃发白的草和起伏的山梁间,隐约可見牧人的一座座冬窝子,屋顶在阳光下发出亮光。铁丝网围栏中是吃草的羊群和一丛丛芨芨草。有的人家草场只是铁丝围栏围起來的一小片狹窄的地方,有的人家草场略大一点,每一户牧民的草场基本上都是年按人口承包划分的规模。 一群大雁列队从盖嶂达坂那边飞來,从朵朵白云间飞向南方,鸣声消失在阿米冈克尔峥嵘的山巅那边。 杜雪峰家的冬窝子就在盖嶂达坂山脚下,这里是阳坡之地,到处有水井,随处可见茂密的芨芨草,草质和相对温暖的气候都适应放牧绵羊。他家房屋旁边有两处远古的遗迹,这是亚欧大草原常见的古墓遗址。方圆五六米的方形石堆,中间有几块白石,半埋在土中的石头覆盖着猩红的千年地衣,如凄凄古血。杜雪峰对他们说附近沒有白石头,这些白石头无疑是从远处运来的。他指给我们看了远处有白石头的地方。他还在这个古迹旁边立了一杆经幡,珍贵的敬畏之心赫然在眼前。 风喁喁低语般地从半人高的芨芨草尖吹过,如潮的声音向他们涌来,夹杂着许多人说话的声音、无数的马蹄声、金属马具和刀剑的碰撞声。抬头远看,白茫茫的草地上阒无人迹。 车凌敦多布想,在无数的黑夜里,在这看似平静的大地上,有多少匈奴时代的鬼魂在这里徘徊。而那深夜月亮之母猫头鹰怪异的笑声又在启示着什么? “仲夏月圆之夜,到旷野或山岭间用心倾听杜鹃的歌声,但是要避开月亮之母——猫头鹰的笑声,还要远远避开朝你嗥叫的白狼……” 杜雪峰的父母给他们端来了酥油奶茶和肥美的羊肉,杜雪峰的母亲属於安江氏族。他們吃过后,告辞了杜雪峰的父母。他们从着杜雪峰的车绕过铁山头上了公路后疾驰返回。 六、柴房子草地——“浩尔万·巴斯图” 秋天,这是最后一段巡游夏日塔拉北境的路。 牧人学者杰奇开车带车凌敦多布和阿努达喇去北境。鄂金尼部落的杰奇思维方式异于常人,牧养牦年和绵羊间隙自学了汉语和英语,而且他一直有着广泛地阅读的习惯。杰奇比车凌敦多布小12岁,也属兔。车凌敦多布记得当年在小镇上中学时,回家走过三岔山口,看见六七岁的杰奇在冰面上玩耍,他坐在用木板和铁丝做成的冰车在冰面上飞快地滑行,一边骂骂咧咧地在冰面上使劲划着铁棍。再后来,车凌敦多布不断听到他博闻广记且常做惊人语,以鬼才般的眼光和知识闻名。杰奇是一个吐伯特语的名字,意为80。大概是他出生时,疼爱他的奶奶80岁了。 杰奇帶他们从马营的西沟进入群山中,途中可見因早年开挖莹石矿被一劈为二的悬崖山岭——令人心碎。从那里上山,他们到了一块夏日塔拉和新城子争夺的牧场,汉名叫做柴房子。这里仍是官方文件叫做“混牧(混合放牧)”的地区——指两个不同行政区域的人混合放牧。2018年夏日塔拉北极村的牧民在这里修建了鄂博,举行了祭祀鄂博的仪式,包括赛马,歌舞等牧人的活动。北极村的雪龙村长要求车凌敦多布起一个新的尧熬尔名字,车凌敦多布认为历史上曾有个尧熬尔人著名的地方叫“浩尔万·巴斯图”,意为三个崖头或三个烽墩。为了记住历史,就用了这个名字,同时也用来代表柴房子的三个古代烽墩。 浩尔万·巴斯图——三个烽墩西边一个断崖面临着一个平川,杰奇开着车一跃而上,从这里北望是永昌新城子,西边山崖下的川地和对面的焉支山都属于山丹军马场。再往西走就可以到匈奴人的单于城遗址(今永固古城)。崖头上的三座烽墩早已坍塌,仅剩土堆和壕沟痕迹,远处一只火红的狐狸一闪即逝。烽墩的土堆上密密地覆盖着年复一年的青草。这个烽墩应该是匈奴人的遗迹。 晚秋山上的冷风似乎想把人的衣服剥个一光二净。细听风中有无数的鬼魂在放声大笑,又像是低声抽泣喃喃自语。而天空那一堆堆灰白或暗黑的冷云之上战事正酣,枪林弹雨,尸山血海。 他们离开烽墩后掉头驶近不远处一座帆布帐篷,从帐篷里出来一个女子。原来是他们鄂金尼部落的女子冬梅,她和来自药罗葛部的丈夫拥平在这里放牧羊群,因为他们沒有草场,许多年来都是租借別人的草场为生。部落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勤勉的牧人。他们在她的帐篷里喝了热茶吃了饼子。冬梅说这里除了夏日塔拉的几户牧民外还有永昌新城子的农民放牧。临行时她还送了阿努达喇一包新采的黃蘑菇,这是夏日塔拉蘑菇中的上品。 风雨不大不小。他們几个人从夏日塔拉南边的群山中绕道走,途中一个山谷里杰奇停下车去看他的牦牛群,而车凌敦多布他们则一人拿一个蛇皮袋子,翻过铁丝围栏,在山坡和灌丛边采蘑菇,秋雨中青草丛里绽放的黄蘑菇如妖娆的琥珀。返回小镇时天已擦黑。 一年过去了,远在异国的车凌敦多布告诉我,西斌前几天来电话告诉他,西斌夫妇夫俩买了一匹红枣骝马,他骑上马去看羊,马到沟垴把他摔了下来,几天无法走路。他妻子骑着这匹马去放羊,突然从旁边跑过的旱獭惊吓了马,把她摔下来,腰被摔伤。 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j/7862.html
- 上一篇文章: 欧洲杯A组前瞻意大利优势明显威尔士恐难
- 下一篇文章: 不是文科生不行,现代汉语是扫盲教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