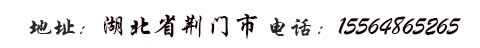入门导览基础书目李维Livy
|
史家简介:李维(Livy) 李维的生平 著名的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用拉丁文称呼的话是提图斯·李维乌斯(TitusLivius)——大概在公元前64年(旧说公元前59年)出生于山内高卢最古老、富足的城市帕塔维乌姆(Patavium,今意大利帕多瓦)。李维的幼年见证了凯撒与庞培的激烈内战;大概在他换上成人托加的时候,随着凯撒的遇刺,血腥的纷争再次笼罩了罗马共和国。在李维33岁时,阿克提乌姆海战(thebattleofActium)终结了长久以来的动荡。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维曾在新生的元首制国家中获得任何军事或政治职位;从他的写作来看,李维恐怕毫无军事经验。不过,几则轶事证明了他曾移居罗马,并与皇室关系密切:奥古斯都半开玩笑地点评他的政治立场为“庞培党人”,以及李维曾鼓励自己的学生、奥古斯都的外甥孙克劳狄(后来的第四任皇帝)写作历史。这些事迹应当发生在李维通过撰述罗马史赢取盛名以后。 传统上认为李维在公元前27年至25年之间开始写作他的名著《建城以来史》(Aburbecondita),但也有一些学者相信他早在后三头内战之初就开始写作。除了历史著作,李维还曾写作哲学对话录,也许是在他开始历史写作以前,但其哲学作品并未留存;昆提良的著作保存了李维致儿子的信的一段残篇。大概在公元12年(旧说17年),李维去世,其生命历程和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几乎重叠。李维去世的地点未知,也许是在其家乡帕塔维乌姆,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位“提图斯·李维乌斯”及其妻子、两个儿子的墓碑(CILV)。 《建城以来史》的结构布局 《建城以来史》(Aburbecondita)是一部一百四十二卷的皇皇巨著,但如今只有前十卷以及第21至45卷留存。凭借古人摘引,特别是一部4世纪的《摘要》(Periochae)的抄本,以及埃及纸草保留下来的的片段摘要(所谓的OxyrhynchusEpitome),我们大致能够复原李维史著的整体框架。 第1-5卷:所谓的第一个“五联卷/五书”(pentad)。在前言以后,第一卷叙述从埃涅阿斯到罗慕路斯建城的罗马“史前史”,以及从罗慕路斯开始的王政时代的“历史”;第二卷至第五卷叙述共和国早期的历史,以高卢之劫的余波结束为止。 第6-10卷:以第二序言开篇,一直记叙到公元前年萨莫奈战争的余波。这五卷和第1-5卷合称李维的第一个十联卷或“前十书”(thefirstdecade)。 第11-15卷:已佚,记叙罗马统一意大利的最后历程。从第12卷开始记叙皮洛士战争。 第16-20卷:已佚。主要记叙第一次布匿战争。 第21-30卷:完好保存的“第三个十联卷/十书”(thethirddecade)。李维用了整整十卷来描绘罗马与汉尼拔之间惊心动魄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并为其再次撰写序言。第26卷开头的卡普阿事件可视为战争的转折点,因此这十卷也可再分为两个五联卷。 第31-35卷:涵盖公元前-年史事,主要记叙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第36-40卷:记录公元前-年史事,聚焦罗马与塞琉古王安条克三世之间的战争。 第41-45卷:抄本缺损较多。涵盖马其顿王佩尔修斯的统治时期(公元前-年),以罗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胜利为结束。 可以看到,主题式的五联卷-十联卷结构是现存李维残篇的基本框架。Stadter主张佚失的第46-卷依然可以按照五联卷-十联卷的结构来划分,例如第-卷是以公元前66至48年前三头的建立与瓦解为主题,其中前五卷以前三头的巅峰时刻——庞培和克拉苏再度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5年)为终止,而后五卷则从公元前54年尤利娅及克拉苏之死开始叙述前三头同盟趋于瓦解的历程,最后以凯撒东渡希腊迎战庞培结束。不过,也有人沿用其他的传统分类法,例如把第-卷视为统一的内战篇章。另外,也有学者主张十五联卷等更大的结构单元。 《建城以来史》的第卷以公元前43年后三头建立、西塞罗被杀结束。不少学者相信李维本来打算就此停笔,不再写作后三头乃至元首制时期的史事。据《摘要》,第卷是在奥古斯都死后才发表的;而且从这一卷开始,《摘要》变得非常简略,五联卷和十联卷的结构也消失了。似乎李维决定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继续叙述罗马向元首制转型期间的历史。李维的著作最后以第卷中对公元前9年的记叙结尾。这究竟是有计划的结尾,还是其他主客观原因(如个人情绪、政治环境、死亡等)使他不得不停笔,难有定论。 自公元前2世纪晚期安提帕特(L.CoeliusAntipater)和法尼乌斯(C.Fannius)的尝试以后,特别是在撒路斯特的发扬下,专题性的近代史写作已经成为罗马史坛的新体裁。但李维的史著(第1卷除外)依然像传统的罗马编年史(Annales)那样,从罗马建城一直写到作者自己的时代;像老加图以来的许多史家那样,李维在内容分配上略古详今。李维也沿用了公元前3世纪以来传统的编年框架(必须注明的是,大祭司年代记对这一框架的直接影响日益受到怀疑):以执政官纪年为基本单元,记叙每年的官职选任、战争与外交、重大政治与宗教事务等内容。但是,在编年的层面上,李维对各年的记述详略并不平均,有时好几年只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他常使用逻辑顺序取代时间顺序来叙述一年内的事件,甚至提前叙述下一年的事件。在必要时,李维常加入超出编年结构的插话,例如第21卷开头关于汉尼拔的追述。在卷次的层面上,各卷长度与时间跨度并不相等,各卷的结尾也不总是与执政官年的结束重合。在宏观层面上,李维精心编排了五联卷-十联卷的结构,并在重要的一组联卷之前撰写序言。显然,李维在篇章结构上的精心安排超越了以往的编年史写作传统,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罗马文学趋于精巧的风尚。 《建城以来史》:方法与风格 与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那种注重材料收集、实地考察的“实践派”史家相比,李维完全是一位书斋中的历史作家。我们不知道李维在书写最后数十卷的近当代历史时搜集了哪些类型的史料,但在现存的诸卷中,李维基本上完全依赖于前人的历史著述。通过考察李维的史料来源,我们发现:李维惯于在叙述的某一个阶段内,以某一种他最信任的材料作为基准,间或以其他材料作为补充或校正。在撰述罗马古史时,李维似乎并不关心正在蓬勃发展的罗马古物学,他倚赖最多的是公元前1世纪的几位编年史家,如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Antias)、李锡尼乌斯·马克尔(LiciniusMacer)和克劳狄乌斯·夸德里加里乌斯(ClaudiusQuadrigarius)。在叙述罗马在地中海的扩张时,波利比乌斯则成为其史著的主要依据。通过对比李维的著作及其前辈史家的存世残篇,学者们得以证实:李维的引用不仅忠实于前人的叙事框架,甚至在事件细节上也常常一丝不苟地进行模仿;在此基础上,他才用其他材料作为插入性的补充。他甚至在否定了夸德里加里乌斯对一桩战斗的定年后,继续大量使用夸德里加里乌斯对这场战斗的描述。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史料批判(Quellenforschung)一直是李维研究的重要方法:学者们煞费苦心地为李维记叙的每一件事实标注可能的来源,并根据内容、文字和立场的相异确定段落之间的不同归属。这样的研究方式显然令李维降格为史料的编辑者与传抄者,而不是具有原创性和批判性的、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历史学者。 与之相对,李维常被看作一位文学大师。撒路斯特不久前将修昔底德的风格引入罗马史坛,但李维拒绝追随撒路斯特的古奥与晦涩。昆提良称李维的文字具有“乳汁的丰沛”(lacteaubertas)。他善于运用不同的风格:在叙述上古历史,以及介绍每年的选举、征兆等事件时,李维刻意采取一种仿古的风格;在战斗场景中,他的文字变得短促有力;但他最擅长的是精心架设的圆周句。李维尤其善于戏剧性的描写:他频繁使用戏剧的反转(Peripeteia)技巧;他对卢克瑞提娅及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自杀的动人叙述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甚至成为近代悲剧的蓝本。但是,相较于唤起读者的情感(pathos)——这是撒路斯特的拿手好戏——李维更重视刻画人物的思想与性格(ethos)。许多学者相信他完成了西塞罗未能完成的事业,也就是以一种奔涌长流、和缓平稳的风格来书写历史,尽管李维的文风与西塞罗相比仍稍显笨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维对于历史(historia)的理解并不在于探究与求真,他所从事的似乎是一种修辞学的工作。 如今,学者们不再把兰克式的史学规范强加于古人,也很少再对李维进行以上的这种身份认定。李维不像波利比乌斯那样热衷于探讨实用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他关心的是以一种适于他那个时代的优美文笔来延续罗马人民的集体记忆。当然,对于实证研究而言,李维仍然是难以替代、不可或缺的资料宝库,但使用时必须谨慎。而在文本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ly/8246.html
- 上一篇文章: 欧洲杯各支球队最终26人大名单全部出炉
- 下一篇文章: 宁死不屈血战ldquo马克西姆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