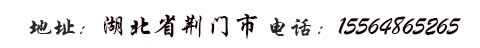社会学家应该把社会事实讲得更加动听,而不
|
银川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凌云吉他”,贵阳吉他高端教育 五岁以上学员家长请咨询 -- 教学地点:中华北路云岩广场黄果树大厦 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 作者 叶启政 当代汉语学界社会学理论大家、原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文载于《社会》年第2期,转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年第6期。 ﹀ 其实,社会学家原本只不过是一个编织故事的艺匠而已。他大体上犹如都市中漫游的行走者,一直处于当下此刻,在一再分岔的街道上一边行走一边浏览着沿途的景观。 一、前言 在20世纪40年代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父亲三不五时会约朋友在家里小酌聊天,在酒酣耳热之际,我父亲总是会发点牢骚,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唉!社会就是这样,有钱就行啦!”当时,我已从学校老师那儿学到一些仁义道德的道理,听了父亲这样的话,总是觉得他太现实、势利,也太庸俗了,甚不以为然。只不过,年幼畏于父威,不敢辩驳。后来,年长当成了专业的社会学家之后,每每回想起幼年时父亲说的这些话,我开始同情起他来。在那个年代,父亲可以说是怀才不遇,日子过得相当郁卒,眼看着诸多公务人员多有贪污的行止,但却能步步高升,日子过得相当顺遂惬意。说真的,当是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里,贪污毋宁地才是“正常”,有钱确实可以使鬼推磨。对一个生活在这般社会样态里的普通百姓来说,诸如我父亲所说的这种话不仅可以理解,若说他是具有现实经验感受的“社会学家”,也是不为过的。 这个幼年的经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总是不免让我这么想:既然人们都是活在人群里,有着各自的生活经验感受,而这些经验感受使得人们对“社会”都会有着特定的看法,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人人都是社会学家”。如此一来,我们立刻会跟着追问:那么,像我这样所谓的专业社会学家又有何用?所谓社会学的知识,与一般人的世俗社会观又有什么不同?其价值何在?这些长期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促使了我在年写了一篇“人人都是社会学家——一个所谓专业社会学家的自白”的文章,刊登在是年8月1日台湾的《自由时报》副刊上。后来,在年,我改写这篇文章,并把内容扩大,以“柳暗花明,回梦一番——社会学者是甚么‘碗糕’”之名收集在《社会学与本土化》一书之中。如今,我又把这样的议题拿出来再次谈论,显然若非对于过去所写这篇文章的谈法感到不足,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做。有鉴于此,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倘若我没有对所以如此做的缘由有所交代,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从年我赴美国留学正式修习社会学开始算起,到年写这篇针对自我之专业角色进行反省的文章,已有28年了。作为一个所谓的专业社会学者,当时的我,虽不敢说见解已经很成熟,但起码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也已浸润了一大段时间,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知识领域的基本内涵有着一定水平的认识。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对社会学家作为学院内的一种专业学者的基本角色与实践操作作为,理应有着相当稳定的定型认知,不太可能有什么更具创意的另类看法才对。情形是这样的话,说真的,我实在没有理由在又过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度把这个议题翻出来重新议论一番。旧菜重炒,只会是了无新意,诚然多此一举。然而,尤其是在已正式从这个专业职场退休下来的情况之下,我又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还想再度来谈论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呢?我有两个理由让自己觉得确实值得要如此去做,在此,试着说出来,与读者们分享。 这四十多年下来,透过“专业社会学者”这个职业角色,我成为社会里的成员。同时,我更是学习经由学院建制化的社会学知识来认识这个社会,并且也以此作为履行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事务的知识底蕴与理据基础。在当下此刻正式从这个专业角色“完全”退下的时刻,对自己过去所经历的种种,心中不免有所感慨,也对社会学作为学院建制中的一门专业领域内涵的社会意义,自然也有些自认更为深刻的想法,觉得有责任说出来,提供给后来人参考。当然,基于这样相当单纯的感性诉求作为理由来圆成写作的动机,难以有足够的力道说服人们接受我的作为。但是,至少我个人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自许并且也不断自勉着。 不过,我自己意识到,单单以志业情感作为理由来支撑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的后盾,毕竟缺乏知性上的正当性,显得太过单薄。我需要提出更具知性的说法,才可能有着最起码的理据来说服大家。为了回应这样的说法,我必须回到过去,从年修改过的那篇文章说起。 在年的文章里,我曾经透过两位美国社会学家奈斯比特(Nisbet,)与米尔斯(Mills,)的说法暗示,一个社会学家一方面必须具有科学态度,但另一方面,更需要的是像传统工匠所展现的那种具有艺术气质的艺匠格局(craftsmanship)。至今,我还是一直坚信,这才是社会学家(可以衍生至所有相关的社会科学者)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可贵的基本学养。只是,在那篇文章里,我并没有将这个观点恰适而充分地发挥,更没有把其体现在社会学家身上所必要彰显的独特认知框架明白地拨点出来,而只是让整个论述游走在专业社会学者同时作为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之间所可能蕴涵的社会意义以及衍生的问题之上。 那么,到底社会学家需要彰显的独特认知框架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来彰显社会学家作为专业学者所内含的知识质性,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是,从当代西方社会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观点可以说是很有价值,也甚具启发性,是颇值得作为切入点(当然,也是分离点)的。简单地说,这个观点是:社会学家营造知识的基本任务即在于挖掘种种社会现象与社会行动背后可以蕴涵的客观“未预期结果”(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吉登斯即相当肯定地断言,未预期结果乃是社会学探索的基本课题,因而,社会学家之知识建构的基本课题即是有关“未预期结果”的阐明与论述建构。下面,我将以这一内蕴于西方社会学知识传统的见解作为起点,申论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与其可能衍生的意涵。 二、从默顿的“未预期结果”说谈起 至少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即已提及“未预期结果”这一概念,后来亚当·斯密也讨论过它;19世纪以来诸多社会思想家,如马克思、韦伯、威廉·冯特、帕累托、库利与索罗金等人也都有所论及。但是,该概念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学界的普遍重现。直到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发表“目的性社会行动的未预期结果一文,特地以此概念作为标题来加以讨论,尤其是到了年,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显性与隐性功能”的章节中,把“未预期结果”与“隐性功能”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运用,由此,“未预期结果”这一概念才逐渐引起社会学家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ly/5328.html
- 上一篇文章: 曾经沧海一位哈尔滨混血作家的忧伤
- 下一篇文章: 尼布甲尼撒的梦与世界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