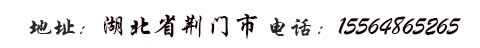11期新翻译荐读罗曼middot罗兰
|
散发型白癜风怎么治 http://pf.39.net/bdfyy/bdfyw/150824/4684516.html 追忆黄金时代 ——18世纪欧洲古典音乐之旅 罗曼·罗兰 孟洁冰译 罗曼?罗兰(年1月29日-年12月30日),20世纪的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评论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理由是,“他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他的小说特点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代表作品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 每一位音乐家都能感觉到,十八世纪末的“古典主义”风格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亨德尔庄重的“前古典主义”风格有天壤之别;古典主义风格具有丰富优美的修辞,严格精确的演绎,学者风范的复调写法,主题鲜明,精神全面;前古典主义风格清晰明了、自然流畅、旋律优美、反映出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时,心底里变幻莫测的情感,这种情感和卢梭的忏悔不相上下,犹如贝多芬和浪漫派作曲家的自白。这两种音乐风格的过渡时期,似乎比人的一生都要漫长。 让我们留心下面这些日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于年去世,亨德尔于年去世,卡尔·海因利希·格劳恩也于年去世。在年,海顿演奏了他的《第一交响曲》。格鲁克创作《奥菲欧与尤丽狄茜》是在年;菲利普·埃马努艾尔·巴赫最早的奏鸣曲创作于年。新交响曲的开创者,捷克天才作曲家约翰·斯塔米茨死于年,早于亨德尔的去世。可见两场伟大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凯泽、哈塞、泰勒曼和曼海姆乐派的音乐风格是伟大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源泉,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属于同一时代。此外,他们的人生也超越了他们自身的价值。早在年(即亨德尔创作《亚历山大盛宴》的第二年,谱写《扫罗》和一系列清唱剧之前),当时还是普鲁士王太子的腓特烈二世,在给奥伦治亲王的信中写道:“亨德尔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他的才华消失殆尽,他的品位不合时宜。” 腓特烈二世把这种“不合时宜”的艺术风格,和他推崇的作曲家卡尔·海因利希·格劳恩的风格做了一番对比。 在年至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申请担任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乐长,接替库瑙的职务,泰勒曼显然比巴赫更受器重,只是因为泰勒曼不愿接受这个职位,巴赫才如愿以偿。年,泰勒曼的音乐生涯刚刚起步,起初默默无闻,不久就超过了声名显赫的库瑙,对新潮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此后,这场运动愈演愈烈。年,扎哈里亚写下了这首《永恒的圣殿》,这首诗对亨德尔、哈塞和格劳恩的评价不相上下,足以反映德国上流社会的看法。他赞扬泰勒曼的诗句如今可能被人们用来称赞巴赫,谈到巴赫和“他富有音乐感的儿子们”,扎哈里亚除了称赞他们的演奏技巧、管风琴和钢琴之王的盛名以外,并没有其他溢美之词。年,历史学家伯尼的看法也同样如此。当然,这些看法让我们感到不胜惊讶。不过我们不能为此感到怒不可遏。我们和这些人隔着两个世纪的岁月,蔑视当时错误评价巴赫和亨德尔的人并没有什么价值。试图理解他们的想法,会更有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巴赫和亨德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态度。他们没有像当今的伟大人物或无名之辈一样,摆出深受误解的姿态。他们没有愤愤不平,甚至和运气更好的竞争对手保持融洽的关系。巴赫和哈塞是知己好友,彼此敬重对方。泰勒曼和亨德尔自少年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泰勒曼和巴赫的交情颇深,巴赫请他做了儿子菲利普·埃马努艾尔的教父。巴赫还把最宠爱的儿子威廉·弗里德曼的音乐教育,托付给了约翰·戈特利布·格劳恩。双方丝毫没有派系斗争的迹象,大家都是互相尊重、彼此欣赏的音乐天才。 让我们本着同样平等同情的包容精神来看待他们。这样并不会有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亨德尔的崇高威望。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身边有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和充满智慧、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理解当时人们对这些音乐家偏好的缘由并非难事。且不说这些音乐家的个人价值多么伟大,正是他们的精神引领了通向十八世纪末期古典主义杰作的道路。如果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亨德尔是两座高山,主宰并终结了一个时代。泰勒曼、哈塞、约梅利和曼海姆乐派则是一条条河流,为自己开辟了通向未来的道路。这些河流奔涌向前,汇入了浩瀚的江河——这就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些河流,却依然仰望远方高耸的山峰。而我们必须对这些改革家心存感激。他们曾经充满活力,把艺术的生命力传到我们手里。 各位读者想必记得,在十七世纪末,法国文艺界出现了古典派和现代派的著名争论,这场争论的发起人是夏尔·佩罗和丰特奈尔,他们反对笛卡尔模仿古代追求进步的理想,20年后,乌达尔·德·拉莫特以理性和现代品味的名义复兴了这一思想。 这场争论超越了发起人的初衷,与欧洲思想的统一运动遥相呼应;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各个艺术领域中,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迹象。凯泽、泰勒曼和马特松这一代人从童年起,就对音乐复古派的代表流露出本能的反感,尤其是擅长对位法的作曲家和精通法规的学者。这场运动起源于凯泽,他对哈塞、格劳恩和马特松(以及亨德尔)产生了极其深远、举足轻重的艺术影响。不过,正是泰勒曼首先明确有力地表达了这种情感。 早在年,泰勒曼面对德国传统音乐理论家普林茨,拿出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态度:他对当今声乐家夸张喧闹的旋律唏嘘哀叹。而我要对那些旧日作曲家音调刺耳的作品付之一笑。 在年,泰勒曼引述了法语诗句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要美化圣典中的古人,与今日作家的水准相提并论。 这正是现代派对守旧派直率坦白的宣言。对他而言,现代派意味着什么呢?现代派就是谱写出美妙旋律的作曲家。 歌声是世间万物的音乐基础,作曲家必然要吟唱笔下的曲调。 泰勒曼补充道,年轻的音乐家应该倾向于意大利的音乐风格和德国的新声乐流派,而不是“老派作曲家,他们可以把对位法的创作发挥得淋漓尽致,却毫无创新之处,他们可以写出十五到二十个协奏声部,可就算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动听的旋律。” 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理论家马特松有同样的看法。年,马特松创办了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批评》,他自豪地宣称,“抛开虚荣心不说,我是第一个坚持强调旋律至上的人。”他认为,此前的作曲家“都忽略了这个音乐中最重要、最精彩、最美妙的元素,就像雄鸡跃过熊熊燃烧的炭火。” 即使马特松不像他说的那样,是第一个强调旋律至上的人,至少也曾为此大声疾呼。在年,马特松为了强调音乐旋律而驳斥对位法大师,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沃尔芬比特尔的伯克梅尔,他和马特松一样博学多才、生性好斗。马特松认为卡农曲和对位法不过是音乐技法的运用,毫无打动人心的力量。为了让他的对手回心转意,他选定支持自己的凯泽、海尼切恩和泰勒曼来担任仲裁人。伯克梅尔最终宣告失败,感谢马特松让他明白了,旋律“才是纯正音乐真正唯一的源泉”。 泰勒曼说过:“演奏乐器的人必定要精通歌曲。” 马特松写道:“无论人们谱写的乐曲是声乐还是器乐,都应该流畅如歌。” 如歌的旋律和歌曲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打破了不同音乐流派之间的障碍,使声乐旋律和歌唱艺术臻于完美的意大利歌剧成为了各种流派的典范。泰勒曼、哈塞和格劳恩的清唱剧,以及当时大量的音乐作品,都融入了歌剧风格。在《音乐爱国者》中,马特松与教会音乐的对位法针锋相对:他希望音乐和其他领域一样,树立一种戏剧风格,因为这种风格能够让作曲家更好地实现宗教音乐的目标,“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他认为,按照“戏剧化”这个词最广泛的理解,世间一切都应该充满戏剧性,流露出对自然的艺术模仿。“所有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事物都充满戏剧性,音乐是戏剧,全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剧场。”这种戏剧风格渗透进了整个音乐艺术领域,甚至包括那些看来没有丝毫关系的音乐流派,比如德国抒情歌曲和器乐曲。 不过与此同时,如果作为普遍典范的歌剧本身没有发生转变,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引进交响性这个新元素,那么风格的转变并不能标志着充满活力的进步。声乐复调的特质在器乐交响乐上失而复得。泰勒曼、哈塞、格劳恩和约梅利用乐队伴奏宣叙调,即管弦乐编曲的宣叙场景征服了歌剧界。在这个领域,他们是音乐界的改革家。管弦乐队一旦被引入戏剧,就能占据上风,维持主导地位。人们徒劳地哀叹歌唱艺术即将消亡。那些支持歌唱艺术、反对旧式对位法的人士,在必要的时候并不担心为管弦乐而牺牲歌唱。尽管约梅利在其他方面对梅塔斯塔齐奥非常尊重,但在这方面反对他的决心却不可动摇。我们必然要听到老派音乐家的抱怨:“人们再也听不到歌声;管弦乐队的声音震耳欲聋。” 早在年,演出歌剧的时候,观众只有看着剧本,才能听懂歌唱家的唱词:乐队伴奏完全淹没了歌唱的声音。在整个十八世纪,歌剧管弦乐得以持续发展。格贝尔说道,“滥用器乐伴奏已经成了时尚潮流。”在戏剧界四处回响的管弦乐,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剧场的束缚,成为戏剧艺术的象征。席伯和马特松并称为德国最有才华的音乐理论家,他早在年就已经开始创作交响序曲,依照贝多芬日后创作的《科里奥兰序曲》和《莱奥诺拉序曲》来说,这部序曲表达了“作品的内涵”。年左右,音乐描写在德国盛行一时,我们可以从马特松在《音乐批评》中的戏谑调侃里看出这一点。这场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受到歌剧的影响,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和罗卡泰利谱写的标题协奏曲风靡了整个欧洲大陆。(本文为节选) 注: 本文发表于《延河》杂志年11期新翻译一栏 本文图片皆来自互联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tq/9662.html
- 上一篇文章: 黑布林英语中文版巴斯克维尔的猎犬06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