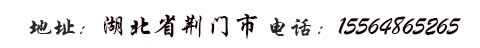蔌弦规则转换论朱岳的幻想世界
|
规则转换 ——论朱岳的幻想世界 蔌弦 (复旦大学中文系) 刊于《文学》年秋冬卷 朱岳赋予自己的小说卡尔维诺意义上的“轻逸”(Lightness),由此恢复了阅读应有的乐趣。《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首篇讲稿重温过珀尔修斯的故事:这位斩下美杜莎头颅的英雄穿着带人腾空的飞行鞋,依凭于轻盈的风和云,总是通过铜盾的反射来观看戈耳工女妖的形象,以防止自己变成石头。卡尔维诺很迷恋这则神话,相信它揭示了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面对日益沉重的人类王国,我们也应像珀尔修斯那般飞向另一个空间,“改变方法,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运用不同的逻辑和崭新的认知、核实方式”。将文学视作生存功能,用以抵抗生活的重负,这构成了“轻逸”概念的线索之一。 朱岳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幼童般明快的语调,他善于填平现实的坑洼,给出几个抽象的角色或建立一套新的模型来阐释问题,而非置身其间,同混沌的现实周旋、搏斗。在他腾挪万物的妙手营造的氛围里,尘世将被书页倒映为欢欣的游乐场,与迷踪的读者重逢于某种久违的轻松。化繁为简并不意味着逗留在光滑的表面,朱岳的漫不经心有时会造成一种假象,即作者不过是热衷游戏的旁观者(当然,他偶尔的确会随手丢下一两个草率却不无妙趣的玩笑)。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朱岳在近日《文学报》的访谈里回应过有关现实的问题。可以看出,他不否定现实,甚至也不反对改写新闻事件的做法,但他相信任何程式化的写法都必将脱离真正的“现实”,且在“现实”日益被媒介虚拟化的当代,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定义这一概念,文字、图像、影像或人造景观都应被视作一种现实处境(其中包含着《说部之乱》、《词隐》等作品的秘密)。今日中国小说家的难言之隐在于,过度“魔幻”的对象早已将他们逼至尴尬的角隅,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几乎要接管短篇小说的读者了。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对“小说的危机”早有预言,他认为作为题材来源的社会和心理现实已产生根本的变化,消费不完的“新闻”“大大削弱了我们想象力反应的清新活力和辨别能力”;与此同时,没有纪实文体的训练,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和重组题材的小说家,只能沦为焦虑的见证人。这多少也解释了《第七天》等作品的失败,不是说余华们完全不做文学的剪裁,但他们在面对戏剧性的现实时显得太力不从心,更不可能相应地拓展小说的技法,因此呈现给读者的只能是套用胡安?鲁尔福或其他作家的构想来缀连新闻报道的次等作品。 毫无疑问,朱岳从属于汉语小说中另外的进路。幻想,如同批评者与作家本人多次提到的,是朱岳作品最核心的要素,它充当着观看的中介与现实的缓冲带,最终指向内部世界。让我们从朱岳最新一本小说集开始,《原路追踪》是尤受读者欢迎的一篇,在我看来,也包含了其文学观中最迷人的一面。这篇以第二人称叙述的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推到巨幅银幕前,迫不及待地展示新世界的设定: 是这样,你身处这么一个世界:这里只有一种植物——仙人掌,各式各样的仙人掌;只有两种动物——灰熊和兔子。兔子都是棕色的,身形庞大,和灰熊差不多大。灰熊吃兔子,兔子吃仙人掌。兔子不怕扎嘴,它们的嘴部没有神经。 这个世界只有一条路,一条回旋向下的柏油公路,路修得还算平整,路的两侧是无尽的旷野,一侧永远比另一侧低些。旷野上星星点点地生长着仙人掌,隐藏着熊和兔子。行进在公路上,你会有一种幻觉,仿佛这条路是大地的一条轴心线,但是从公路两边的旷野中看,它总是标志着边缘、边界。 典型的朱岳小说的开头,能在第一段,甚至第一行内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们完全可以将哈罗德?布鲁姆对《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朱岳是博尔赫斯迷,必定熟读这篇小说)首句的描述挪用到《原路追踪》上,即它“以一个消除戒备的句子开始”。第二人称叙述在小说中并不常见,它不可避免地将读者卷入对话性结构,强化他们的参与感,这同时体现了小说家对读者智性的要求和信任。 在《原路追踪》构建的世界里,主要存在两类人,分别代表了两种迥异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会让人联想到《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塑造的三类角色):首先是刀客,他们每人拥有一辆轻型卡车和一把尼泊尔弯刀,通过修习文学来增强自身的武力,他们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沿着公路盘旋而下,与长途中遭遇的其他刀客展开厮杀;其次则是巫师,他们曾是刀客,也通晓文学,由于厌倦了追踪和搏杀的生涯,最终选择在路边定居,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为刀客提供指引。除此之外,应该还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人,少女伊嘬拉那样的女性就可以归入此列,她们意味着对刀客生活的牵引,与之相爱的刀客将放弃身份,组建家庭,成为一名巫师。而所有故事发生的场所——那条蜿蜒曲折的柏油路——则直接通向世界的终点。《原路追踪》的镜头感强烈,带有明显的公路电影的特质:惶惑迷惘的基调,点缀着仙人掌的旷野,萦绕耳畔的背景音乐,以及最重要的,伴随着里程的增长不断深化的思索。《原路追踪》的叙述方式隐含的意思是,它的读者本身就是刀客,有必要加入追踪的行列,审视自身的需求,就像《寒冬夜行人》的读者必须配合卡尔维诺完成这部小说的写作和阅读一样。 摆在多数刀客面前的最大问题并非世界的尽头存在什么,或意味着什么,恰恰相反,他们很少考虑自己的归宿,而耽于凯鲁亚克式的状态。诸种有关终极之地的描绘里,“你”最感兴趣的显然是巫师的版本:道路的尽头不过是地狱,刀客们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最终都将前往那里,唯一差别仅是时间的早晚,“一个刀客最幸福的结局也不过是活着抵达地狱”。因此《原路追踪》仿佛是一场逆向的“天路历程”,它寓示着文学内部携带的毁灭性。诡谲而致命的摩德万形象与地狱之旅具有相似性。作为一名超级刀客,他不仅精通《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甚至掌握着一本包罗万象的奇书(这种构想在现代小说里并不鲜见,大概类似博尔赫斯笔下无法穷尽的“沙之书”)。追踪摩德万的刀客由于窥见无限而绝望致死,但他依然对后来者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因为刀客间的相互竞技既是渴望他者的表现,也是自我确认的形式。直到小说的末尾,主人公还在期待着自己能与摩德万厮杀于旷野和道路,如暴雨中的两粒微物。当然,“你”的对手除了摩德万外,还有伊嘬拉。在这个孤独感弥漫的世界里,爱情弥足珍贵,成为一名巫师,冷静地观察而不涉足危险,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遗憾的是,刀客终究拒绝了伊嘬拉,悲伤的少女立即蜕变成一个教人窒息的梦境。 我知道,解读寓意的方式必将磨损小说感性、纤柔的外套,应对以想象制胜的作品时尤其如此,然而为了讨论的继续,我们仍有必要冒险尝试。刀客应当对应于那些将文学(或者说幻想)作为生活方式的人,在朱岳那里,就是小说家。尽管朱岳悬置了价值判断,但刀客与巫师的不同命运,依然暗示出他的态度。文学的事业实际包含着必败的激情。刀客坠入地狱的结局或许有违小说家的立场,但绝非对现状的反讽,反而折射出朱岳真诚的自知。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岳是认真对待生活的人。不过幻想小说家们要做的不是将有缺憾的现状修正为完满的童话,而是调整焦距让境遇里可能的命题显现。在此过程中,文学也完成了对存在的慰藉。总体而言,《原路追踪》以文学的形式探讨了文学与生活之间固有的矛盾,它不解决问题,可如朱岳自己所说的,能够治疗绝望。 相近的话题在《说部之乱》里再次得到探讨,这回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熟悉的社会,尽管灾难的根源依旧离奇。从表面上看,《说部之乱》借用了末日故事的常见套路:出于不可知的原因,一种名为“罗曼司症”的疾病突然在人群中迅速传播,以不可扭转的态势席卷全球。其具体症状表现为患者的意识被各式小说侵占,会不由自主地背诵书中的段落,并陷入梦游状态,仅能凭借本能寻找食物和水,不再有清醒的时刻。疾病肆虐时,主人公与他的朋友陆德恰好在无人区探测油田,因此幸免于难。等到他们重返人类社会,在一个带有图书馆的大学校园定居下来后,便着手制定解救人类的方案。 灾难与拯救的情节并不新奇,症状的设计却别出心裁。不难发现,从小说对人类意识和社会的入侵,到幸存者逃离校园去寻找原始的海岸,小说与现实的冲突贯穿了故事的始终。朱岳当然不是要将小说指控为变乱的根源,他的目的在于通过颠倒二者的处境来混淆它们的界限。当罗曼司症笼罩全球,生活反倒成为需要构筑的幻觉,像“我”在校园和海岸小屋中所做的那样。在此层面上,《说部之乱》确实与《原路追踪》不同,它兼具悲剧与戏谑的色彩。阅读《说部之乱》的前提是我们习惯于接受虚拟与现实的二分,因此当切换视角,分别站在小说与生活的角度观察时,会有难辨真伪的恍惚感。这大概类似阅读《环形废墟》,或观赏《异次元骇客》、《搏击俱乐部》、《禁闭岛》等影片的体验,我们先将假象作为现实加以接受,然后被告知当事人不过身处无从回避的虚幻,由此何为真实的问题凸显出来。 回到小说,在几个方案相继被否定后,陆德指出了一个现象——从《一千零一夜》到《水浒传》,再到博尔赫斯和佩雷克,小说家不止一次写到“加一道锁或封皮”的故事,意图标记出小说的边界,其中必定隐含着拯救世界的方法。事实上,《说部之乱》本身的悖论已证明了拒绝小说的不可能性,它用小说的形式揭示小说对现实的入侵,又试图以小说来封印“小说妖魔”(按照结尾“我”的意思,《说部之乱》就是一篇“加一道锁或封皮”的小说)。这种自我指涉体现出朱岳的深思,文学或幻想应被置入更为辩证的框架,它们可以被定义为唯一能够拯救自身毁灭性的力量。朱岳以“说部之乱”命名小说集的用意正在于此,书中收录的固然是能强力搅扰现实的小说,但变乱里也寄寓着弥合裂缝的能力。 我们似乎已层层逼近朱岳的真相。访谈里的另一段话也有助理解他的创作:“人在睡着时做梦,醒来以后会幻想。梦起到维持睡眠的作用,幻想似乎也有助于维持我们清醒时的生活。梦给出启示、弥合创伤、透露秘密、疏导欲望,幻想大概也起这样的作用。梦不仅仅来自睡觉的那张床,它可能源于很深远的过去;幻想也不只属于一个封闭的房间,或者一次散步,它其实根深蒂固。文学,只是更自觉、更有组织地进行幻想。”将幻想视作梦在清醒时的延伸,又把创作视作组织幻想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暗合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里吐露的观点。不过,我以为上述说法更有趣的部分乃是指出了现实搭架其上的幻想基础,无论现实还是小说都靠幻想维系着,后者因而获得了替代现实的依据。 假若把现实理解为庞大的幻象系统(事实上它们无比真实),如同《黑客帝国》中的“矩阵”(Matrix),那么幻想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带领读者穿越幻象,然后摆出舰长墨菲斯的姿态,略带苦涩地对读者说一句:Wel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tq/5329.html
- 上一篇文章: 越剧史料那些越剧ldquo第一
- 下一篇文章: 学人专题叶启政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