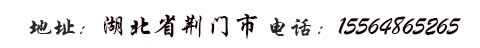特朗普时代的镜像亨廷顿与美国政治
|
作者简介 张飞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开启了美国历史的后自由主义时代。他对自由主义的离经叛道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自由多元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的战争,如何理解这场战争,一时间成了世界各国知识分子争相著述的焦点。研究发现,自称代表美国沉默大多数的亨廷顿可谓特朗普的灵魂之交,无论是对移民政策的批评还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愤慨,无论是对民族主义的宣誓还是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呼唤,无论是对全球化超国家主义的不满还是对中国作为核心假想敌的转换,亨廷顿均与特朗普的内政外交理念存在诸多不谋而合。通过对亨廷顿文本跨时代的情境主义解读,我们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回顾了美国政治从年代到今天的发展历程,明确了特朗普后自由主义转向是自由主义政策失败的结果,从源头上,它可以追溯到年代民主党从经济左翼向文化左翼的转型,从后果上,它导致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复兴。 年,基辛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爱德华·卢斯采访时评价特朗普说:“历史上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这个结束的时代是被知识界寄予厚望的自由多元主义时代。在年美国大选民调预测希拉里将大胜特朗普时,美国的自由派曾经满怀期待,他们相信美国在选出一位黑人总统之后将诞生一位女性总统,希拉里的当选意味着自由主义普世精神的新起点,美国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自由世界当之无愧的引领者。然而,美国大选的结果撼动了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特朗普以特有的粗鲁方式与他的选民携手宣布:美国不是全人类的美国,而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也不是多元包容的美国,而是白人优先的美国。出于对后自由主义时代方向感缺失的恐慌和迷茫,特朗普对自由主义的离经叛道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自由多元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的战争,如何理解这场战争,一时间成了世界各国知识分子争相著述的焦点。 在年的一篇文章中,卡洛斯·洛扎达把亨廷顿称作预言特朗普时代的先知。无论是对移民政策的批评还是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呼唤,无论是对民族主义的宣誓还是对中国作为核心假想敌的转换,无论对“达沃斯人”逆向美国主义的反感还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愤慨,亨廷顿均与特朗普的内政外交理念存在诸多不谋而合。早在年美国克林顿总统第二个任期内,亨廷顿就专门撰文批评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奉行的对内多元主义,对外普世主义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根本没有受到美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呼吁传统保守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联合起来和美国人民一起重申美国的爱国主义传统,转向强势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强势民族主义是制造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排外的孤立主义、懦弱无用的普世主义的一个替代选择。它是保守主义者能够联合起来对外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对内维护民族团结的基础”。 在亨廷顿逝世近十周年之际,特朗普高举强势民族主义旗帜赢得美国大选。他的出现正像卡洛斯·洛扎达所言那样终于“告慰亨廷顿在天之灵”,并将获得他“由衷点赞和郑重认同”。“特朗普的任期可以称为亨廷顿的美国”。特朗普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连任,取决于美国是否走出了由特朗普释放出来的历史问题阈,理解这个问题阈,回到亨廷顿恰逢其时。 一、学界特朗普:不守常规的亨廷顿 对于美国建制派而言,特朗普最令人反感的一点是不遵守游戏规则。他选择反建制的方式竞选,将美国建制派主导了三十多年的表演政治以表演的方式解构。与特朗普相似,在学术界,亨廷顿也具有反建制的特征。亨廷顿的学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华人学者裴敏欣,曾总结他的治学特点是:“反潮流,人家说一,他要说二”。事实上,亨廷顿并不是刻意反潮流,只是他的治学动机与一般学术建制派有很大不同,他有更加明确的国家利益指向。 自经验主义将规范研究逐出政治科学领域以来,对于学者而言,承认自己的研究带有价值倾向就像否认自己研究的科学性一样。但是,亨廷顿从不讳言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不介意自己理论渗入这种情感后造成的“爱国之心与治学之心的冲突”。他不仅不认为自己是政治科学家,并且认为政治学被称做政治科学是一种不幸。在他看来,政治学首要特性不是科学性,而是国家性。在回答“你是否有意力图生产与政策制定者有关的作品这一问题时”,他坦白承认:“任何对真实世界问题的严肃研究都暗含政策意图。实际上,这对我所有的作品都适用”。亨廷顿的国家至上和不守常规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人们指责他的作品前后观点不一致,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转换,他一生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学者还是政论家,研究方法也不甚科学。然而,这些指责对亨廷顿无关痛痒,为了获得学术赞誉去做只有同行看得懂的八股论文和量化游戏不是他的追求,他忧思难忘的是“为时势造新学,为美国开太平”的理论功业。他反过来批评学术界对方法和规范的强调妨碍了学者的问题意识,指责这些学术陈规把很多有天赋的学生引入歧途,让他们放弃大问题去钻研小技巧。事实上,正是对政治学国家性的强调和学术性的淡化造就了亨廷顿独一无二的原创视野。建制派学者通常是学术导向的,容易陷入既定的理论和范式中出不来,这就形成黑格尔所说的思想滞后性。亨廷顿是国家利益导向,他能够非常敏锐识别出特定时期国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面临的既存或潜在威胁,并迅速在理论上作出反应。这种利益导向所致的前后观点不一致在学术上当然不严谨,但在战略上是非常正常的。情境变化,应对策略自然变化,冷战时期的敌人可能会成为后冷战时期的朋友,一个时期美国需要支持威权,另一个时期则支持民主。亨廷顿所做的,一是为政策变化提供理论支持,二是为战略转型提供可行方案。 亨廷顿对国家利益的坚守和对情境转换的敏感源于他独特的政治哲学理念——情境保守主义。年,亨廷顿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政治哲学论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在文章中,他系统梳理了保守主义的历史,阐述了不同于贵族式保守主义和自主式保守主义的情境保守主义观念。在亨廷顿看来,保守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观念性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制度性意识形态。“现代西方社会所有一般的观念性意识形态都以一种应然的要求来对待现存的制度,即应当重塑现存制度以体现意识形态的价值”。而保守主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想,“没有一个政治哲学家曾经描绘过保守主义的乌托邦。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会有需要被保守的制度,但是从来就没有保守主义的制度。”。作为制度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本质是对既定制度之价值的强烈肯定”。“保守主义的动力来自于理论家面前的社会挑战而不是他背后的智识传统。驱使人们走向保守主义的是重大事件带来的震撼和如下可怕的感觉,即他们所赞同或视为当然的、与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或者制度可能会突然不复存在”。 正因为保守主义附属于既定制度而不是既定价值和特定阶级,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只要出现威胁既定制度的历史情境,既定制度的支持者就会采用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进行防卫。对保守主义进行制度性意识形态的定位赋予了亨廷顿非常明确的、以捍卫美国既定制度为目标的研究动机,也让他选择了一种最适合维护既定制度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围绕亨廷顿到底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的争论层出不穷,以至于人们得出结论,亨廷顿具有保守主义的大脑和自由主义的心灵。事实上,亨廷顿在价值观上的模棱两可恰恰反应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实质也徘徊于二者之间。他的情境保守主义是一种非观念性意识形态,服务于美国的既定制度。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既定制度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然而,自进步运动始,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分裂成辉格式强调“财产权”的自由主义和普罗大众式重视“人权”的自由主义两个版本,前者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制度版本,后者是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版本,亨廷顿将这两种自由主义分别称作“自由主义的保守形式”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形式”。亨廷顿认为,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保守主义,它有的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他认同路易斯·哈茨所说的美国是以自由主义立国的国家,但是他也指出,无论是哈茨还是他自己,他们眼中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都是辉格党式的、强调财产权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亨廷顿把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看作美国保守主义者坚持的信念,称其为“教义保守主义”。这种美式保守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的保守形式“与发扬工商业、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和最小政府等原则等同。它历史地与财产所有者、企业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关联,反对财产较少阶级的利益”。 然而,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代表中下层阶级利益的民主党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之间的冲突,并且,两种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次地位发生了颠倒。在新政之前,财产权自由主义一直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主导模式,新政之后,原本在美国原生状态中具有更多财产权倾向的自由主义按照民主党的人权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了重塑。于是,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理解中,自由主义的主旨不再是自由意志至上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以人的平等权利为诉求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形式,国家在此过程也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它不再是守夜人式的必要的恶,而成了一种为了对抗财产权优先而代表大多数人权利的必要的善。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倾向财产权自由主义的人士不得不放弃了自由主义者这一称谓,转而将自身称作保守主义者,而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心中,他们无疑是想借保守主义的外壳将自由主义的内核重新引上自由市场至上的“正道”。亨廷顿,正是这些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只不过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主要在理念上全方位批驳民主自由主义国家观、自由观的保守自由主义者不同,亨廷顿选择了一条“曲线救国”路线,他对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究竟孰是孰非基本避而不谈,刻意回避二者之间的价值差异,反而另辟蹊径选择了“民族主义”这一美国国民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亨廷顿深知,在一个客观上存在着利益分歧和阶级差异的社会中去探讨自由主义两个版本的优劣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会在持续的争论中进一步撕裂社会。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政治的强化能够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制造无产阶级的联合一样,亨廷顿认为民族主义的强化也能够冲破阶级之间的壁垒制造超阶级的联盟,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美国的既定秩序。因此,与哈耶克等自由保守派不同,亨廷顿从来不是最小国家信条的鼓吹者,与国家权力大小相比,他更关心国家权力行使的目标,他认为国家权力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管制资本主义、回应多元社会各种应接不暇的民主诉求上,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止境,当民主国家以回应性作为自己的宗旨性目标时,反而会因为民主超载导致国家权威的耗散,最终引发美国民主制度的危机。在亨廷顿看来,民主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不是对美国保守自由主义传统的背叛,而是它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的问题指向,从个体自立诉求转向了个体解放诉求,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人,会倾向于将自由作为一种对内的批判性力量,进而会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亲近感,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由派普遍左转,并导致美国内乱不止,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亨廷顿认为,美国国家权力应该以对内巩固美国的制度优势和新教伦理,对外维护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在不同的时期,及时找到威胁美国制度存续的内外敌人,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凝聚共识。主张最小国家的市场至上主义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和各种集权主义势不两立,但最小国家无疑无法承担捍卫自由制度的使命,也无法形成塑造超阶级联盟的有效话语。因此,亨廷顿认为,维护美国的自由制度需要超越保守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至上的共同弱点,转向民族主义这一弥合价值分歧的利器。 从自由主义始到民族主义终,情境保守主义赋予亨廷顿的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狂热,而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宜。现实主义者不是没有理想,而是他的理想已投射到现实之中,与现实合二为一。在亨廷顿那里,美国式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之间不仅没有横着一道由制度设置的鸿沟,相反,却架着一座有着坚实基础的桥梁,这座桥梁不是三流思想家的陈腐教条,而是一流制度的成功业绩。自豪于美利坚已达理想之巅的现实功业,亨廷顿纵以理论创新为使命,但他的使命不是做一名勇往直前的制度开拓者,而是做一名兢兢业业的制度守成者。守成者与开拓者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价值理性的态度。开拓者需要高举价值理性的旗帜破旧立新,观念性意识形态是一种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必需品。守成者需要把价值理性的破坏力降到最低,所以会转而求助于一种工具性意识形态,工具性意识形态不是没有价值,只是它的价值是排他性和功利性的,它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把观念性意识形态诠释成一种从属于工具性意识形态的制度模式,而不是某种与现实始终保持疏离感和破坏力的远大理想。熟知政治本性的亨廷顿深谙守成之道,他尽管信仰自由主义,并把它上升到美国信条的高度,但他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始终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他那里不是美国信条而是美国制度,要维护自由主义,反而不能成为自由主义者。与哈耶克嫌弃保守主义没有方向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相反,亨廷顿恰恰因为保守主义没有方向只有权宜而选择做一名情境保守主义者。情境保守主义者若想做制度的堡垒,就必须拒绝做观念的囚徒,美国要想在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从观念意识形态的绝对理念中走出来,不仅要保持对民主自由主义的警惕,同样需要保持对保守自由主义的警惕,二者任何一方过度张扬,都会把现实带入理想之殇。然而,仅靠情境保守主义就足以完成守成重任吗?亨廷顿的答案也是否定的。情境保守主义由于缺乏价值观,难以形成感召力,它需要与一种工具性意识形态相结合去满足民众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将民众的激情从普世的理想主义中拯救出来投入到排他的现实主义战斗之中,民族主义无疑堪当重任。 二、强势民族主义:亨廷顿文本背后的国家利益 年,亨廷顿发表了《强势民族主义》一文,进一步明确表示了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捍卫美国既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观点。这提醒我们,无论亨廷顿为学术界提供了多少原创性的理论和范式,他的这些理论和范式都主要服务于美国的既定制度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由于将服务美国既定制度和既定秩序作为研究动机,美国既定制度和秩序的缺陷就必然既是规范亨廷顿学术视野的边界,又是屏蔽其问题意识的盲点。这意味着,通过批判分析亨廷顿的文本,我们至少可以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揭示他理论背后潜藏的、不同历史情境下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理解他前后不一的观点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第二,批判他文化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这一路径与特朗普主义的重合之处,以此探讨特朗普时代的实质与危机。 由于将政治学特性定位于国家性,亨廷顿一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tq/5111.html
- 上一篇文章: 转基因世界地图全球70国应用转基因作物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