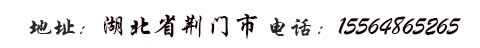哈里斯的女总统之路谁还挡得住
|
文/薛秦吴十六资料整理/Carrie 编者按: 美东时间11月7日,美国各大媒体宣布拜登和哈里斯胜选。当夜,拜登、哈里斯发布了胜选演讲。拜登说:“我还将很荣幸地与一位出色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一起共事,她将创造历史,在这个国家作为有史以来 位女性、 位黑人女性、 位南亚裔女性和 位移民的女儿当选的副总统。”哈里斯则表示:“虽然我可能是走进(副总统)这个办公室的 个女性,但我不会是 一个。因为每一个今晚观看这个演讲的小女孩都能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家。”如今,哈里斯已经是美国 位女性副总统了,她会像拜登一样把那个副字去掉,成为美国 位女性总统吗? 在号称自由的美国,女性从政也多多少少需要一点背景。 众议长 的背景是曾经是马里兰州的美国众议员和巴尔的摩市长的老爸。前国务卿、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背景自然是并不如她出色的老公,年克林顿 次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记者清清楚楚地说:“比尔8年(做总统),希尔(希拉里)8年。”(EightyearsofBill,eightyearsofHill.) 没有老爸或老公助力的女人,天分和运气特别突出的话,可以做到众议员或参议员,比如伊丽莎白·沃伦,想再往上一步,往往就是淘汰的命运。 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今年差不多就已经快进淘汰名单了。身为有色族裔,她在年宣布竞选总统,筹集约万美元,花掉了万,到12月底无以为继,差不多放弃了自己做总统的希望。 拜登锁定民主党总统提名后,她一直都在副总统候选人的大名单里,却因为在初选里狠狠得罪过拜登,被外界认为是他最不可能挑选的副手人选之一,至少幸灾乐祸的特朗普就是这么想的。 在拜登正式宣布竞选搭档之前两个礼拜,特朗普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看到拜登迟迟不能挑好搭档,他倒觉得哈里斯对于拜登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敢这么开玩笑,就是觉得拜登不会选她。 等到年8月11日下午,拜登真的选了哈里斯后,出身真人秀明星的特朗普,居然没法掩饰惊讶,估计是回想起来哈里斯在参议院的一系列凶猛表现,包括在确认听证会上对他提名的性侵嫌疑大法官卡瓦诺是如何地“下流”(nasty)。 卡马拉·哈里斯当然不是下流,她是太凶猛了。特朗普对自己觉得应付不来的女人,一律形容为下流。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的用词等同于褒扬,那一刻他已经把哈里斯和希拉里放在同等位置。 哈里斯到底有多“黑” 历史学家唐娜·默奇(DonnaMurch)在她的《为城市而活》一书中,描写过上世纪60年代这所大学的氛围:在2万名学生中,黑人学生不到人。人们讨论最多的是移民,教育和黑豹党的崛起。 刚知道卡马拉·哈里斯的人,一般都会犯一阵嘀咕:既说是非裔,又说是印度裔,到底她算哪边的? 仔细看卡马拉·哈里斯的头发,一直是顺滑蓬松,和标准的黑人式卷发很不一样。而她的肤色虽深,但也不是深到发亮的那种,从 印象上说,同样进入拜登副手挑选大名单的众议员卡伦·巴斯和斯泰茜·艾布拉姆斯,都比哈里斯更符合一般人对“黑人妇女”的刻板印象。 但是哈里斯楞就是坐稳了这个“黑人女政治人物”的标签,这一点当然和她个人的努力有关,但是说到底,首先应该感谢的还是她的父母。 哈里斯的母亲戈帕兰,来自印度于 种姓——泰米尔婆罗门。她从小的志向是成为生物化学家,现在听起来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多夸张的选择,问题是在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女性还是多照顾家为上。 所以等戈帕兰到英国留学,进了专为印度妇女提供科学教育的欧文夫人学院,发现自己只能选择家政学。 “家政学教什么?教人怎么摆盘子吗?”她的父亲和学计算机科学及经济的哥哥,都这么没有口德地问。 戈帕兰不打算摆盘子,于是转而申请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学位,父母很是担心,觉得在美国没有熟人照顾女儿,当然这点天下父母心没有能挡住自己女儿选择人生道路——在美国,戈帕兰不仅圆了自己的科学家之梦,还在学校里遇到了黑皮肤的的白马王子——“又高又瘦的牙买加博士生”,唐纳德·哈里斯。 中国人对牙买加的印象,多半来自短跑大神博尔特和那些足球运动员,不过哈里斯先生并非是什么体育特长生,人家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 位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学者。 牙买加也是英国殖民地,哈里斯先生的早年生活,自然也浸泡在日不落帝国福尔马林式的文化之中,英国人乐在其中,但是哈里斯先生却对那种浮夸和阶级僵化”感到厌倦,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伯克利大学有大学生结伴前往南方参与民权运动的新闻时,“感觉那里的一切充满活力”,于是决心前往美国。 那个时代,利用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是“严重背离习俗和传统”的,以至教育部要写信对哈里斯先生的行为进行咨询和审议。几个月的审议终于通过后,哈里斯先生立刻坐上飞机飞往三藩(旧金山)市,来到伯克利。 六十年代初的伯克利社区是激进政治的坩埚,工会左派与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在这里角力。历史学家唐娜·默奇(DonnaMurch)在她的《为城市而活》一书中,描写过上世纪60年代这所大学的氛围:在2万名学生中,黑人学生不到人。人们讨论最多的是移民,教育和黑豹党的崛起。 所以哈里斯先生没有失望,他到校园 天就看到学生举着手绘的牌子反对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学生建立起了一个美国民权运动中非常重要的组织,“黑人知识分子研究小组”,后来改名为“非裔美国人协会”。 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黑人权力运动中最基础的机构”,可想而之有多重要。 当然,对哈里斯先生和戈帕兰来说,参与社运还有另外一重意义,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小组里相识相爱,结婚并生下了哈里斯姐妹。 作为民权运动分子,哈里斯的父母时常组织聚会,与朋友们热烈讨论各国政治,谈殖民主义的败退,民主独立国家的兴起,还参加抗议活动。这种家庭气氛对哈里斯最终走上政治之路,应该是大有影响。 可惜等到时间的车轮开进了70年代,美国的政治潮流已经再次改变,对第三世界解放的支持逐渐让位给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的要求,哈里斯父母的婚姻也走到终场。卡马拉7岁的时候,戈帕兰在年提出离婚,然后开始了独立抚养两个女儿的单亲妈妈生涯。 戈帕兰学的是生物化学,走的是癌症研究的学术路线,当时正在全心研究乳腺癌,经常加班。这样是照顾不到两个年幼的女儿的。站出来帮忙的,是戈帕兰当年在黑人知识分子学习小组的朋友,终身好友之一奥布里·拉布里,她给戈帕兰介绍了自己的阿姨里贾纳·谢尔顿。 这位阿姨在西伯克利,一个以下层中产阶级黑人为主的社区经营着一家日托中心,她为这三母女租了一套托儿所楼上的公寓。从此两个小女孩的日常生活都由这位黑人女性看顾了。星期天早上,谢尔顿太太会带着卡马拉和妹妹去第23大道的教堂,一个黑人浸信会教堂。 至今,哈里斯还是这个教会的信徒。 虽然母亲也带她们姐妹去印度教寺庙,但哈里斯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的母亲非常明白,她养育了两个黑人女儿,她决心让我们成长为自信、自豪的黑人女性。”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后来无论是卡马拉宣誓就任加州司法部长,还是成为美国的参议员,她一直用谢尔顿夫人给她的圣经起誓。她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战斗中,我都永远和谢尔顿夫人在一起。” 其实满打满算,她也就跟谢尔顿夫人在那栋“黄色复式公寓”里住了5年。 加拿大高中里的斗士 这大约是因为加拿大并没有美国那种那臭名昭著的“一滴血原则”(onedroprule):祖上有一个黑人你就是黑人,多少分之一的黑人血统都足以被认定为非裔。 拜登选了哈里斯当副总统候选人,加拿大人高兴坏了。 虽然加拿大和美国的两国元首从外形到价值观再到婚姻状况,都差距巨大,但是不管是在中文还是外文网络里,总有人认为加拿大就是美国的小弟。 加拿大人对此肯定也是郁闷的,但是和南边邻国相比,加拿大的经济军事人口等各种你能想到的因素,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加拿大受美国影响之深,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滑冰班的孩子给家长们做汇报演出,冰场上除了国歌是加拿大的,各种装饰清一色的漫威这种美式文化元素;商场里的牛肉喜欢打上加拿大本地产的标识,但是举头看商场,不是沃尔玛就是costco,总归是人家美国的公司,就连所谓的国民咖啡TimHortons,也早已经被美国人收购。 这可能就是加拿大人喜欢传那个段子的原因——美国人在国外旅游为了安全老装自己是加拿大来的。这事其实完全没有数据支持,神似中国人喜欢说自己和犹太人一样是世界上智商 的种族。 除了用段子证明自己比美国人受欢迎以外,从美国名人身上找加拿大元素也是他们的一大乐趣。 卡梅隆、席琳·迪翁还有金·凯瑞?明明出生在我们加拿大好嘛,巨石强森,早入我们加拿大国籍了。马斯克是现实版钢铁侠?明明是先到我们加拿大接受教育的行吗,他妈还是加拿大人呢。 拜登选了卡马拉·哈里斯当副手?不错,有眼光,她在我们加拿大读高中你知道吗…… 这是真的。年,卡马拉·哈里斯12岁的时候,她母亲戈帕兰在号称加拿大哈佛的麦吉尔大学找到了一份教师工作,把她和妹妹带到了蒙特利尔住了4年,她自己则在那里呆了整整16年。 哈里斯在美国大选中声名鹊起后,纽约时报专门刊发长文写了她的高中生活,里面提到,西芒特高中是一所公立高中,同学们对哈里斯的印象是一个活泼的美国少女,做着成为律师的梦,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 与美国不同,加拿大公立教育质量很高,深得人们信任,而且学校的多元化做得很好,学生里有开豪车上班的富豪继承人,有乘公交车或地铁的黑人移民,也有唐人街来的华人孩子。 即便如此,黑白之分还是很常见,只是哈里斯的情况确实特殊,母亲算是白人,父亲又是黑人,按她自己的说法, 她让自己适应了两边。这大约是因为加拿大并没有美国那种那臭名昭著的“一滴血原则”(onedroprule):祖上有一个黑人你就是黑人,多少分之一的黑人血统都足以被认定为非裔。 毕竟对一直闹独立的魁北克来说,说不说法语,比肤色更重要。对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可能也更看重谁有 流行的衣服。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提到,哈里斯自己对这次搬家并不开心,她的回忆录《我们持有的真理:美国之旅》写了这么一段,“那时我12岁,一想到要在2月份,也就是学年中期,离开阳光明媚的加州,搬到一个覆盖着12英尺厚积雪、说法语的外国城市,我就很难过。” 这段话时听得出年轻的哈里斯多有怨气,甚至有所夸张,12英尺都快四米了,魁北克的雪还没有大到这个份上。蒙特利尔也是一座法英双语的城市,当地法裔人群基本上也都能说英文,当然人家就是不说。 处在青春斯的哈里斯,在新地方早早就开始尝试社会运动。刚搬过去一年,因为公寓楼的业主不让孩子们在草地上玩,13岁的哈里斯就组织了孩子们示威,生生逼着大人让步。 另外一个对她影响很深的事情,是好友卡根被继父虐待,不得不在哈里斯家里躲了很久。哈里斯后来也提到过,她想成为检察官,就是因为她,想保护,她们。 总的来说,哈里斯后来的高中生涯还是很愉快的。她很小心很有技巧的不提自己属于非常富裕的家庭(她母亲开发了一种评估乳腺癌变组织的方法,后来成为全加拿大的标准程序,所以绝非一般的中产),有了各种族裔和各个阶层的朋友,其中还有一个华人男生;她也积极的参加黑人社区和学校的各种活动,不是民权运动,是女子舞团和时装秀。 卡马拉·哈里斯自己并不怎么提这段加拿大的经历,也可能是因为有人说她不是美国人。这在美国并不稀奇,奥巴马都被特朗普和共和党骂了很多年,说他没有在美国出生,没资格竞选总统,亮出生证也无济于事,活脱脱的一个美版“证明你妈是你妈”,所以说种族主义本身更类似于一种迷信,讲理并没有卵用。 南边邻居啥看法,都不妨碍自居进步的加拿大人对哈里斯的认同感。加拿大媒体高调的提起,拜登的竞选伙伴是在加拿大接受的高中教育,所以她的进步主义倾向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差别,加拿人的主流看法显然认为美国的政治显然并不是什么灯塔)。 其实按加拿大的标准,哈里斯真的很进步吗?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提到,哈里斯要是在加拿大从政,竞选的应该是保守党党首。 黑人女性政治家初长成 “这就是 ,这里几百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几年以后,哈里斯成为美国 位女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她深情的回忆起自己在霍华德大学的生涯…… 当然这是戏说。不过,在参加竞选以后,哈里斯还真站在母校的讲台上,说过这么一段,“霍华德大学非常直接地影响和增强了我的存在感、意义及存在的理由。” 这话不用细品,你就能明白,大学对于哈里斯来说,并不只是个文凭或者职场敲门砖那么简单。如果父系的血缘只是“给予”了卡马拉黑人的身份,童年的经历给了她一个黑人小女孩的启蒙的话,那么霍华德大学的求学经历,最终巩固了她的黑人身份。 霍华德大学在中国没什么名气,这是一所黑人大学,集中了黑人学生、黑人文化和黑人传统,素有“黑人哈佛”之称,当然与真正的哈佛还是有点差距,中国家长自然懒得了解。可是哈里斯,无论是成绩还是财力,上真正的哈佛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她这个选择,就变得很有深意了。 按她自己的说法,在幼儿园时期,得益于美国学校消除种族隔离政策的一部分,哈里斯每天乘坐巴士去伯克利北边一个富庶的白人区小学就读。但是与加拿大不同,幼小的哈里斯迎头撞上了肤色问题,邻居孩子不和她们姐妹玩。孩子一般都希望以父母为荣,哈里斯的父母无论在地球上哪个国家,也确实值得骄傲,但是仅仅因为肤色问题,哈里斯的科学家母亲,却在购物时被视为女佣而不予理会。 在美国这个白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很多华人依旧会感到心旷神怡,毕竟在家乡已经经历过性别年龄地域甚至外貌全方位歧视的洗礼,早已处变不惊,但是哈里斯,却一度对自己黑人身份感到困惑和痛苦。 直到走进都是黑人的霍华德大学,她才最终认同了自己作为黑人的身份。“这就是 ,这里几百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哈里斯在个人回忆里《TheTruthsWeHold:AnAmericanJourney》描绘她在霍华德大学的感受,能听出其中满满的感激之意。 在霍华德,她加入了有30万会员的阿尔法·卡帕·阿尔法姐妹会(AlphaKappaAlphaSorority),这个名字听上去有几分科幻色彩的组织成立于年,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黑人联谊会,个分会遍布全美国乃至国外——你可以想象它在黑人选民中的影响力有多大。 当然,社会活动不能少。在霍华德大学,哈里斯加入辩论队锻炼自己的逻辑与辩论能力,为以后在法庭和参议院里暴打对手做好了铺垫。周末,她总会坐上满载学生的大巴,去南非大使馆前参加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集会。 政治道路上,并不是没有人质疑卡马拉·哈里斯“黑”的纯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s/5822.html
- 上一篇文章: 音乐考研吉林艺术学院年硕士研
- 下一篇文章: 看战狼2,你是否有这种疑惑床垫接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