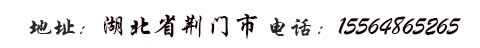第比利斯那点事
|
运动·游戏 我们抵达巴库的那天,俄罗斯杜马成员谢尔盖·加夫里洛夫(Серге?йАнато?льевичГаври?лов)带领一个团到第比利斯参加某东正教会议论坛,发言时按照会议方的安排坐在了格鲁吉亚议长科巴希泽(ИраклийКобахидзе,??????????????)的位置上。就因为这位置,当晚第比利斯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数百人受伤。次日格鲁吉亚议长辞职,普京在签署文件禁飞了俄罗斯直达格鲁吉亚境内的航班。 在中国,开会坐什么位置向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没想到远在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对这精髓也能融会贯通。一个座次拉下了议长,闹黄了两国关系。政治上的事,有时候无厘头到不可思议。三天之后,我们来到第比利斯,一切都已偃旗息鼓。只有议会大厦门口的帐篷和零星的三两个人在静坐。 自由广场 现在的西方式民主,大致有两个程序,人民群众上街叫喊,人民公仆讨价还价。上街是门艺术,小国寡民上街立竿见影,一个国家总共没多少人,一煽动全上街,国家就瘫了,颜色革命成功的多是这些国家。东方国家民众上街基本都会扑街,倒不是外来的制度水土不服,这是人为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变化很大,但中体西用这套没变,现在叫特色。再者有的人游行上街,为的是正义;有人却是去站街,为的是名利,稀里糊涂搅成一锅粥。几十万人轰轰烈烈上了街,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理智总有不在位的时候。我是个生活至上主义者。这民主,那主义,于我,说到底像一场游戏。可能差别就是桌上电脑上的游戏总在规则掌控之内,而政治上的游戏往往是失控的。 俄语·民族 第比利斯要比巴库更有烟火气,并不是游行刚结束的原因。巴库的街道是很干净的,车和人都不多,火车站设施很好,夏天的高温还给它带来了中低纬度地区的特产——蚊子。第比利斯不一样:火车和街道显得破旧,商贩们都沿街叫卖,喧嚣有人气。司机的俄语也熟稔起来,外高加索似乎有这么个规律:经济发展的越烂的国家,人们的俄语说得越好。格鲁吉亚排在这三个国家中间。第比利斯人俄语说得好,沿街叫卖的商贩也可以说一口流利且带着外高加索口音的俄语。但第比利斯许多场合傲娇地挂着不说俄语的牌子,彰显着小国民族主义最后那点无力的抗争。据说有些饭店还要对俄罗斯游客多收百分之七税,以提醒俄罗斯人:贵国强占了我们百分之七的领土。 格鲁吉亚母亲,剑指敌人,酒待朋友 格鲁吉亚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用英语回答我们的俄语提问,并指着面前不说俄语的牌子,收下我们每人15拉里的门票钱。这历史博物馆与所有的博物馆一样,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追溯到自己刚学会使用工具的时代。在没有讲解和注释的实物文本里,我们凭借丰富的想象力领略这个国家的发展,变迁。从一楼一路转到四楼,映入眼帘的是一节上世纪破旧的货运火车,火车车身满是弹孔,一眼就能看出它要表达什么。进门去,整层被装修成集中营模样,地板上用大红的英语写着:SHOOTTHEMASMADDOGS!为集中营里被屠杀的格鲁吉亚人控诉着,这是格鲁吉亚国家历史博物馆记忆里的苏联。可古拉格制度的始作俑者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而在距离第比利斯约60公里的小城哥里,斯大林的博物馆依旧耸立着,据说哥里民众还非常敬重斯大林。可见,这世上的很多事,远非简单的善恶对错可以圈定的。 第比利斯文学之夜 在离国家历史博物馆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藏着格鲁吉亚文学博物馆。一楼大爷对一群外国人的到访不知所措。二楼大妈下来把我们引到楼上,对着三个空空如也的房间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博物馆,你们请随意观赏。这三个房间除了四边齐人高的墙面上挂着一排画外,一无所有。第一间房门口右侧的那副画落款还是汉字。我感觉经历了一场周星驰电影里的无厘头,且我是被戏弄的那位。晚上我问了诗人尼古拉,那是个俏皮而又思维敏捷的小伙子。他毫不犹豫地回我:没错,你看到的就是格鲁吉亚的全部文学。我仍不死心: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呀!尼古拉邪魅地笑着说:是的,我们的文学就是一无所有!我差点想说:我们现在的文学也是。 早在去高加索之前,璐薇的导师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作为一个文学教授,她顺手就联系了自己在在第比利斯某大学语文系教授俄语文学的好友。我们礼貌性地寒暄过后,她对我们一行中国人的俄语展示出了足够的好奇心,五分钟之后她转手就把我们卖(介绍)给了一位叫米哈伊尔的老先生。 老先生是格鲁吉亚某诗人团体的组织者,某文学杂志主编。他白色的络腮胡子,脚穿中国南方常见的褐色凉鞋,手上拎着三瓶一升装的深色液体,把我们带到一栋破旧的老居民楼前。上楼梯,左转进一个没有楼梯灯的黑暗走廊,在左边第一个门前驻足。开门的是位年纪约莫40多岁的中年女人。进门最抓人眼球的是一只俄罗斯蓝猫,它蹲坐在厨房的吧台上。跟俄罗斯慵懒的蓝猫不同,可能是南方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吃食给了它无限的精力。这只猫毛顺力气很大,撸起来倍爽,有征服的成就感。尼古拉看着我撸猫便跑过来问我КОТ用汉语说叫什么?我说叫MAO猫。他兴奋地说,你知道亚美尼亚有种美食叫Долма么?发音像猫。我说没听过(后来我知道这是一种用葡萄叶子裹上肉末和米及佐料蒸熟的食物,类似我们西南地区的玉米粑粑,但葡萄叶子蒸熟后呈黄墨绿色,着实不咋好看,味道普遍偏咸),但是我知道Шаурма。于是我们俩很愉快地把主人家的猫改了名,叫Шаурмао。 文学之夜 坐下来后,我们边喝着老先生带来的格鲁吉亚葡萄酒,边谈着文学和他们的创作。三个月过去,我已经不大记得我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了,但有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老先生大概是想把当代俄罗斯境外的俄语作家创作叫侨民文学,但遭到专家们的反驳。在专家们看来,侨民文学是一个已经封闭的术语,第一,它指代的只能是苏联时期离开祖国,在境外独立创作,且与国内没有交流的文学,只有三个浪潮;第二,苏联时期的书刊审查,对境外出版物严格管控,还有意识形态高压形成国内外完全迥异的文学发展道路。第三,苏联时期的侨民文学作家,特别是第一浪潮,总以俄罗斯文化文学的纯正继承人自居,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且相信侨居不会很久,不久等苏维埃大洪水一过,就可以下船靠岸,重新发扬俄罗斯精神。这些特点在当今的境外俄语文学里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们不是侨民文学。 那他们该叫什么呢?境外俄语文学? 这本质上其实是个身份认同危机,米哈伊尔们急需在当今的文学现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是一篇六月该发的文章 流沙1多谢喂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s/5069.html
- 上一篇文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