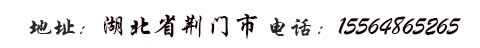采金现场记
|
一 正值瓜果飘香之际,我乘车从兰州出发,经过凉州、甘州、肃州,穿过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沙漠,又走瓜州抵敦煌。我此行的目标是阿克塞。 车过敦煌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驶去。时值中午,极目晴空,但见瀚海戈壁,浩浩无际,云山渺渺,大漠苍茫。在蒸腾的暑气之中,股股旋风拔地而起,旋入太空,经久不散。又见无垠荒漠,涛涛海水,状似鱼鳞密织,时而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时而又息波秋水,泛起涟漪。在天地相接之处,滔滔海水(实为地气)之上的一片迷幻雾气中,显出了高楼大厦,亭台楼阁,繁华闹市。这些景物又若隐若现,被掩映在五光十色的奇光异彩的纱幕之中。 “真是奇景!”我内心赞叹着,不由得想起明人戴弁的诗句:“北上高楼接大荒,塞原如掌思茫茫。朔风怒卷黄如雾,夜月轻笼淡似霜。弱水西流青海远,将台南去黑水长。远人遥指斜阳外,蔓草含烟古战场。” 在我感叹之际,汽车已飞出数百公里,向阿尔金山爬去。司机小黎告诉我,说前边的绿洲就是阿克塞县境了。我的精神又为之一振,放眼望去,但见阿尔金山的主峰,巍巍挺拔,似倚天宝剑。山顶积雪在阳光之下,银光熠熠,玲珑剔透。山下绿洲中白杨红柳,郁郁葱葱。 在出发之前,我曾翻过史料,据载:阿克塞的哈萨克族是新疆哈萨克族的一部分,年至年间,因不满新疆军阀的压榨,3万余人,背井离乡,流浪到阿克塞一带,直到解放后才定居下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首府博罗转井镇,坐落于当金山脚下,长草沟外。当年,有蒙古人在此游牧,用石头于山包上垒起了鄂博,故称博罗转井。其镇位于海拔多公尺,人数仅有千余。 我到阿克塞的目的是了解该县武警中队卫生员蔡忠全的事迹的。蔡忠全年入伍,原在酒泉支队机关里当卫生员,后改为志愿兵,调到了阿克塞,一呆就是几年。阿克塞牧民多,却多过着游牧生活,因此居住分散,有病不得治疗,他便经常深入到牧民之中,为牧民看病。久之,被牧民誉为“马背医生”。 当蔡忠民站在我面前时,我仔细地打量他,他黑黑的面孔,中等个头,浑身上下都透着草原人憨厚的气质。他眼睛不大,厚厚的嘴唇,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健谈的人。 我和他见面时,他正收拾药箱。我忙问他:“小蔡,你这是干什么去?要到草原给牧民看病?” 我这次来有个打算,想跟小蔡到草原上走几天,到牧民中了解一下他的事迹。小蔡听了我的问话,说:“我不是去草原,要去哈尔腾,那里采金人死了不少了,又没有医生,我去救他们。” 我的心头一动,跟小蔡到采金处看看,不更好么,一来了解小蔡,二来了解采金人的生活。——我一直想了解采金人,但一直没遇时机。于是,我决定跟小蔡走一趟。 小蔡听了我的决定后,他打量了我一下,说:“那个地方你可去不了,海拔多公尺哩。” “不怕。”我说:“别人能去的,我也能去。峨眉山我还爬过哩!” 小蔡睁大眼望着我,他不知道峨眉山有多高(峨眉山海拔多公尺)。见我决心很大便说:“我们明天走吧,有些药我还没凑齐。” 我同意他的安排。 小蔡去做上山准备工作。我让指导员到县里给我找些有关黄金的资料,熟悉一下采金场的基本情况,也算是采访的准备工作吧。 材料上这样记载着:河西走廊各地蕴藏着丰富的金矿。大戈壁的许多河流中,如大通河、疏勒河、金强河、哈溪河等及其支流的古河床,以及火山岩冲积、洪积扇底部,由于古生界火山岩原岩中的沙金,经外因的长期侵蚀剥落与流水冲积,逆呈水平状布于各河道。象金强河上游的金场,哈溪河上游的天桥沟、兜金坡、毛毛山北麓的芨芨滩、金洞沟,扎毛沟、黑土沟,大通河东岸的天堂乡一带,均为沙金的主要产地。而今各处尚有淘金遗址,说明境内的淘金历史悠久。金分两种,一曰“麸.金”,形同麦皮,小似针尖,细如毫毛;一曰“豆金”,形类豆瓣,尖圆不等,小者若粟,大者成块,有重至数克乃至百十克的,成色一般在九成以上。这些是走廊平川的金矿。 哈尔腾及党河南北山麓,有着历史上久享盛名的82道金沟。从明初到解放前夕的多年间,嘉峪关内外的人民一直在此开采金矿,官方征收课金。据史料载:乾隆五十二年(公元年)请定南北二山额夫名采金,每夫每月应纳课金3分3厘,每年三月初十日开厂,九月初九日封厂,计收课金两。粗估冒算,数百年间,仅官方征收的课金,已达到数万两到10多万两。 指导员大略地给我讲了他听说的采金场的情况。 自打改革之后,那些在贫困中挣扎半生的农民,从窑洞、泥坯房内走了出来,怀着发财之梦,涌向了哈尔腾山谷,涌向了道道金沟。尔后,各种各样的传说从山内传到山外,甚至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说某某一进山就挖了块狗头金,他乐坏了,抱着狗头金回了家,没想到路上狗头金跑了,原因是他没有那个命。又说某某草绳捆腰进的山,一年下来,腰缠百万贯。这许许多多的传闻,把那些终年和土地打交道的庄稼汉,成群结伙的吸了过去。指导员又把一张报纸给了我,在这张报纸上,一位记者记录了采金者进山的情景。他写道:“他们乘坐着卡车、手扶拖拉机。车,头尾相衔,一辆接一辆,一眼望不到头,足有5里长。车辆的两侧是骑马骑驴的。牲口,一头跟一头,排得象车队一样长。机声隆隆,喇叭嘀嘀,驴声嗷嗷,马蹄得得。所经之处,尘土飞扬,掩天蔽日。不由使人想起杜甫笔下的‘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的浩浩荡荡的出征队伍。” 据不完全统计,西北数省、区的个体采金者,数以万计地涌向这里,去寻找金子般的天堂。 天堂真的那么容易寻找吗? 二 这天晚上,小蔡给我讲起他两上哈尔腾的情况—— 哈尔腾那地方,以前我没去过,地图上标着海拔多公尺。别看山高,金子可多呀,说有人一锨能挖个金娃娃。我们总队也在那里办了个金矿。有十几名战士和许多民工。1月前,战士小王从山上下来回兰州,经过阿克塞时到中队吃饭,他告诉我,说山上挖金子的民工已经死了30多人了,都是因为感冒而死的。山上没有医生,有药也不会吃,差不多每天都死人。我问他,感冒怎么会死人呢?他也说不准。我听了很着急,决心上山救人。我把想法对指导员讲了,指导员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就用自己的元存款买了药,做好了进山的准备。正巧总队有汽车进山,我就搭车跟去了。山上没有路,汽车在铺满卵石的河坝上晃动。车行得很慢,晃了一天,到了黄金管理站。这个管理站说白了就是卡子,卡那些采金不纳税的人。我们在这里睡下。第二天晚上,我们赶到了一个牧民点,那里有几户牧民,在这里又睡了一夜。从阿克塞到哈尔腾,多公里的路,汽车跑了4天才到。由于山太高了,下了车我都喘不过气。抬眼一看,山谷中到处是挖金子的人,山坡坡上搭着破旧的帐篷。采金的大都是青壮年,还有不少十三四岁的娃娃。这些人多是西北的回回,自从5月份山上冰雪溶化后,他们就来到了这里,抢占地盘。他们每伙人都有老板坐镇,他们多是老板的雇工。 那天,我喘着气来到采金人中。当他们听说我是医生时,好多人都围了上来,我见许多人嘴肿得厚厚的,脖子、脸、手都黄了,不仅走路吃力,连呼吸都困难。这当儿,有几个民工对我说:“医生,帮帮忙吧,那儿有个人要死了。” 我赶紧过去一看,得病的是个20岁左右的青年,他话也不能说了,我摸摸他的脉,脉也没有了,真的快要死掉。我连忙拿出银针,刚要扎,旁边一人结结巴巴地问:“这,一针要多……多少钱?” 听着这话,我不禁想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话,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他们却先想到钱。也难怪,这年头干啥事离开钱也不行啊!我告诉他们,我治病只收药钱,公价。周围的人听了,长长地吐了口气。我给那个青年扎了许多针。过了一会儿,那青年睁开了眼,面色也缓过来了,他眼含着泪望着我,想说甚,却没有力气说出。刚好有拖拉机下山,我就让拖拉机把他拉走了。 接着,我又抢救其他的有病的采金娃。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采金娃中死的大都是18到20岁的年轻人,而且病状都是感冒。我给他们扎针、开药。忙的1分钟空闲都没有。太阳快落时,又有几个人跑到了我的面前,说他们那里有几个人快死了,请我去治治。我见这里的重病人都处置完了,就要这里轻些的病人先等一等,我拖着沉重的步子,随那些人来到了一面山坡上。只见七八个采金人躺在帐篷里,一个年长些的回回给他们念经。其中一人已经死掉了。另外的几个人也快死了。我赶紧进行抢救。当这几个人脱离了危险时,天已经大黑了。那些采金人对我的到来别提多感激了。他们把舍不得吃的蒸不熟的馒头、土豆拿给我吃。你不知道,由于山高路远,从山下运去的粮菜都十分的宝贵。他们还给我端来了永远烧不开的水。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嘴唇也肿了起来,这可能是高山缺氧所致。 晚上,我就住在回回的帐篷里。他们把皮褥子给我铺上,又给我盖上厚厚的被子。他们说山上夜里很冷。睡到半夜,我的气喘不上来了。只好坐着,一直坐到天明,我胡乱吃了点东西,又拖着疲倦纶身子继续给他们看病。 我治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采金工地。那些工头们都纷纷派人请我去他们那里,并引相出高价。竞从50元抬到,、元……最后,一家工头竟答应一天给我元。我说:“钱,我不要,我是个武警战士,是来救人的。” 得病的人到处都是,我一个人累死也看不过来的。我真恨不得会分身法,把自己分到各条沟谷去抢救那些生命。 第三天,山上下起了大雪,刮起了狂风,刮得人站不住脚。气候的突然变化,使采金人得病的更多了。我为了多抢救病人,就顶着风雪,从这个帐篷到了那个帐篷。几天后,我带的药都用完了,只好下山取药。 下来时,我又搭乘总队采金的汽车。途中,汽车陷到了山谷水中,排气管又被堵死,车开不动了。我们只有7个人,看着车没有办法,而周围也没有人烟。天晚了,大家只好蹲在山凹里过夜。夜里冷得很,为了防备狼,我们点了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堆坐着,一直坐到天亮。天亮后,过来一队采金的回回,他们帮着把汽车推了上来。 当我回到中队后,战友们见了我都吓了一跳,我上山才几天,不仅嘴唇肿了,脸上也暴了一层皮,黑糊糊的,不成个人样儿了。大家劝我不要再去了,说弄不好把命搭进去。我想到那些病得快死的采金人,就又准备了许多药,二进哈尔腾。 我二进哈尔腾是骑马去的。一个人整整走了6天。我本来还想去老地方,没想到走到一个叫西沟的地方,就被一群路过的采金人看到了,他们见我的马背驮着药箱,问我是不是医生。见我点头后,他们急急说:“东沟那边死了30多人啦,还有不少病人,你快去吧,准能发大财!” 我告诉他们,说我看病不为钱,他们似乎不信,都用怀疑的眼神儿看我。我决计去东沟。便问他们路怎么走。刚好有两个采金人要到东沟去,我就与他们同行。 东沟与西沟隔着一座大山。山上没有路,马也不能骑,只好沿着山的缓坡向上爬,爬了3个多小时,到了东沟。那里采金人病的更多,而且得皮肤病的最多,大概是潮湿和不干净的缘故。 经过我两个多小时的抢救,3个快要死的人被我救活了。可还有几个人死掉了,没办法,我一个人救不过来呀。 这天夜里又下起了大雪,大雪铺天盖地。山上的气候就这样,白天热时热的人光膀子,可天气一变就下雪,下冰雹,许多人大概是不适应这气候,又加上山高缺氧才病的。第二天,大雪还不停得下,大风刮得什么都看不见,许多帐篷都掀翻了,采金人都披着被子坐着。真是受罪呀,若不是为了金子,为了生存,谁也不会来这里的。 东沟东头的一伙采金的听说我在这里治病,派人把我请去,我冒着风雪,走三步歇两步的到了那里,那些重病人都在那里喘气。我给他们扎针,吃药。其实,药就是普通的药,那些药是救不了他们的命的,那些人活了下来,主要靠针灸,还有他们的命运。我针灸的技术也不算高明,可在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卫生员,也算上名医了。 说到这儿,小蔡叹口气说:“采金处每天都病死人,可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人的意志。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那一次,我呆了10多天、药用完了,才赶下山。正要三进哈尔腾,你就来了。” 听着小蔡的叙述,一个神秘的世界浮在我的脑海:汹涌的人流,黄金和性命成等号,高山之巅弓腰抡镐的人…… 我决定上去!小蔡和中队干部们还是劝我,怕我吃不消,但我决心已下,他们也只好依从我了。 三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了。汽车吃力地在盘山的砂石路上爬着,直奔当金山口。 当金山地处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中段,山岭峻峭,地势险要,是山南山北的交通要道。由瓜州经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的公路干线经此山盘绕而过。当金山西部是阿尔金山,东部是党河南山,野牛脊山。 到底是日本产的车时速快,比起我们国产的解放牌、还有拖拉机要快得多。第一天,我们到达了建设乡政府所在地塔喀尔巴斯陶。该乡辖有哈尔腾和乌呼图两个行政村。说是乡所在地,其实也只有少数人家。房舍简陋(整个阿克塞县也只有0口人)。当晚,我们宿在了乡政府。主人是很好客的,他们听说我们是远方客人,很高兴,杀了羊,做的手抓羊肉,摆上马奶酒和吉尼特。吉尼特是用小米粉、奶豆腐粉与酥油、白砂糖合在一起做成的食品。小蔡告诉我,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才摆上吉尼特。 来阿克塞之前,我从有关资料中看到哈萨克族有史以来就以热情好客闻名。他们中间有一句话:“祖先的一部分遗产是留给客人的。” 我们坐在“斯尔马克”(花毡)上。这时,羊肉煮熟了,主人端来了一盆水请大家洗手。重新铺好餐布,用盘子端来了香喷喷的肉。接着,主人又端起马奶酒,唱起了祝酒歌:“我们是个牧民人,放声歌唱欢山谷,客人一来全家欢乐,好客迎送是我们的高尚。” 主人的马奶酒做的味道好极了。马奶酒是哈萨克族牧人的名贵饮料。哈萨克人称其为“合木考”,其制法是将新挤的鲜马奶盛于沙巴(用大牲畜皮制成的酿袋)之中,不断用奶杵加以搅拌,使其发酵,微带酸味,即可饮用。 这一晚,主人客人都喝得面红耳热。 从建设乡往前行就没有路了,只有沿着河床的卵石而行。日本的车因为是“车中贵族”,所以不能跑了,而中国农家用的拖拉机和“解放牌”,成了这条路的主要交通工具。 我们搭乘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沿着颠簸不平的河谷行进。 这是大哈尔腾河河谷。在阿克塞境内有3条河流。即:大哈尔腾河、小哈尔腾河、安南坝河。大哈尔腾河发源于野牛脊山和土尔根达坂山,由野马沟、青马沟、头道沟、克什塔斯乌增和玉勒昆塔斯乌增等主要支流汇合而成。最后流入小苏干湖和大苏干湖。小哈尔腾河发源于土尔根达坂山,汇流于乌呼图。其水多顺沟流入河漠,盐碱极大。这两条河的最大特点是流出山时都潜入地下,变成地下河,尔后又从地下流出地面。拖拉机在河谷中行走时,我放眼望去,但见林木葱茏,苍翠碧绿。其树种多为毛柳、胡杨、怪柳,亦有成片松柏。越往上行,树木越矮。小蔡告诉我,说这山中药材特别多。雪莲、大芸、麻黄、锁阳,沙参……到处都是。 “真是座宝山。”我内心赞叹着,却懒的张口,只感到胸口象压了块石头,气不够用。小蔡看到我这情形,说:“这里有海拔多了。” 拖拉机艰难地奔跑到太阳落山时,我们到了黄金管理站。 黄金管理站在采金人口中称为“卡子”、“关口”,他们为了逃税,千方百计逃避卡子的检查。 我打量了一下这个地方,地形确实不错,两边为峭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几间破房子,房子里坐着几个彪形大汉,其中有两个穿公安制服的,还有两个武警战士。不知是因为山上的紫外线照射还是经常不洗脸的缘故,一个个都黑糊糊的。但那身架,1人能顶上3人。我略问了一下,他们的任务是“以逸待劳”,用他们的强壮身板,对付那些已经在山上耗尽力气的采金人,使他们留下税钱——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采金人衣袋里的金子往外拿时,是要心疼的。 我们宿在了这里。晚上,吃的是玉米面摇疙瘩汤,盐水拌野蒜、拌沙葱。山下的菜不好往上运,这些人也只好这么苦着。好在他们也都苦惯了。我想:假如他们工作在深圳,若让他们到这里来,怕是要重金相聘了。而这些人,虽然工资微薄,但他们已经很满足。——中国老百姓是极容易满足的。何况还有那么多采金人怕他们。 山高缺氧,我睡不着觉,就同管理站的几个人闲聊,听他们讲抓堵采金人的事。 黄金管理站的老张拿出一份材料说:“你看看这些数字就明白了,这还是个不完全的统计。” 我接过一看,是一份油印的通报。标明了历年采金者数字。特抄录如下:年,人;年,1人;年,5人;年,1人;年,17人;年,0人;年,人;年,000人;年,10人。 采金人数是直线上升的。而国家收购的金子却成倒比。人均交金数从年的每人0.两,下降到年的0.两。这说明,大部分黄金流失了。而十几万采金大军,靠这十几(多到几十个人)相堵,是绝难完成的。 老张向我讲起采金者的事。他点了一支烟说:“年那工夫,办采金证的人不多,人们还没明白这生财之道。到了年就不得了啦,在企业管理局门前,办证的人山人海,跟赶庙会似的。成千上万人都涌在门前,而办理采金证的只有两三个人,哪里忙的过来?有的等了几天都办不到手。一个采金证年只交10元钱(这钱是作为土地植被破坏管理费)。第三年涨到30元、50元。当这成千上万人涌到企业局门前时。采金证竟80元、元的直线上升。而那些办证的连眉头都不皱。” “为什么呢?”我问。 老张摇摇头说:“这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的事。元买个采金证,有的发了财,有的丢了命。” “是不是采金证收的钱还少,价格政策不合理?”我又问。 “这根本就无法用价格杠杆来解决。”老张说:“有许多人的证由采金王出钱。”他见我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坐地老板,他雇许多民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划地为界。这些人都腰缠百万贯,发大财了。那一点点钱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在乎的。” 公安局的老李插话说:“这些买证的人还算好的,还有不少人连证也不买。”他补充说:“咱们这里与青海交界。不少人从青海办证到这边来挖,当我们缉查队伍赶到时,他们跑过省界,我们干瞪眼没办法。另外,采金人也太多。我们几十个人的缉查队到了那里,跟小船儿到了大海一样。那些人甭动手,一人一口唾沫也够我们受的。”他接着讲了这样一件事:“去年的夏天,有人报告,说从青海那边过来不少人到野牛脊山北面挖金子。野牛脊山是我们甘肃同青海的省界。山象牛脊,所以叫野牛脊山。山北边是甘肃,山南是青海。因为山北金子多,山南人经常涌过来。他们采完了就走。那一次我们二十几个人骑马赶到山上。青海采金人见我们来了,把家什扔下,跑到了山顶。他们后退一步就是青海,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伙几十人因为找到了好矿苗,没有舍得马上离开,被我们堵住了。他们见我们来了,几十个人聚在了一起,每个人手中都握着铁锨,满脸怒气,摆出了一副与我们拼命的架势。我们身上虽然有枪,可也不敢上膛,采金人多是西北的,他们性格倔强,敢拼命,不怕死。而且在山顶上还有不少青海采金人,他们远远地看着我们的举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真要打起来,我们是占不着多少便宜的。如果我们真的放了枪,把那些人激怒了,他们会从山上涌下来,敢把我们骨头都砸断。可我们也不能后退呀。这样,双方对峙着。我们向前移,他们不动,我们再向前移,他们还不动,彼此相距十几米了。他们当中一人冲我们喊:‘是朋友就让条路!’这路当然不能让。可我们每个人心中也明白,不让路就意味着要有一场恶战将发生。这时,他们当中走出个大汉来,那人光着膀子,拍着胸膛说:‘你们不是有枪吗?(我们在上山之前,曾朝天鸣过枪),朝这儿打!’我们自然不能打。那人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他身后的人也步步紧跟。就这样,这伙人从我们眼前跑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是敌人,无非是为了多挖点金子,少给国家点钱,这个场面是很难处理的。那一次,我们把他们挖金子的工具都收走了,带不走的就破坏了,待我们下山之后,那些人又涌了过来,家什没了,又运来新的,真是没办法呀。” 我们的话题又扯到了这“卡子”上。我问他们:“你们能堵住采金偷税人吗?” 老张笑道:“鱼过千张网,网网都有鱼,总还是能堵着一些的。” 他说起这样一件事—— 去年夏末的一天,有多采金人乘坐拖拉机下了山。、这些人是做了准备的。他们到了卡子前,从车上涌下十几个人来,搬开了道杆,几十辆车冲了过去。这些采金者的举动,是他们守卡人始料不及的。几百人一下就冲了过去。如果这些人的举动得逞,那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的人冲卡子。于是,有关部门动员了公安、武警、工商等单位人员,前堵后追,将其中大部分人抓获,并对他们进行了重罚。 听到这里,我问:“以后还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老张连连吸了几口烟说:“一个要偷税,一个要卡,还能平静吗?反正双方每天都在动心眼儿。”他感慨地说:“说来我们堵卡还是手软。” 他讲起了马步芳、马步青当年堵卡的事。在“河西二马”统治青海间,对采金者实行军事管制,每10个采金者就有1个兵看管,并对采金人实行军事化,金场有重兵相围,若把金子带出去,真比插翅还难。就这样,那些采金人还是把金子带了出去。他们利用金子不生锈,不感染伤口的特点,在腿上割了大口子,把金粒子塞进去,慢慢的长好,待离开金场后,再从腿内把金子取出来。这真是痛苦之举,而为了金子,这些采金人忍受了一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采金人的秘密终被马家发现了。马步芳下令!割肉取金。采金者遂被排成队,脱光了衣服,逐个检查,几百名有伤疤的人被拉出队伍中。这些人开始不招,当几个人的腿被砍断,惨叫不绝时,其他的人都跪倒在地。之后,每人用刀子割开肉,从血肉中取出金粒子。 听罢老张讲的故事,我说:“咱门是社会主义国家,哪能象马步芳那样干?” 老张把手中烟头一扔说:“话虽如此,总还是厉害点才好,不然这样下去,用不上几年,祁连山、阿尔金山都能刨翻个儿。水土还能不流失吗?” 我默然无语,老张的话也不无道理。 四 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拖拉机到管理站就不走了。恰好有采金老板送货的一辆卡车,老板也在车上,他听说我们要上山,巴不得讨好我们,慨然应允,并要我坐在驾驶楼内。这是个黄河牌大卡车,车楼内能坐3人,老板也坐在了里边。 越往上跑越难走,车身晃荡着,行的很慢。由于海拔太高,我感到头裂耳鸣。为了采访,我还是忍着头痛,同这老板交谈起来。 这个老板姓马,三十六七岁,是个回回。别看年岁不大,却很能干,尤其是识别金矿,很有一手。他叫马长东,车上人都称呼他为马掌柜,我也叫他马掌柜。马掌柜跟我讲,他的父亲、祖父都是当地的采金王,能识金路,能看地3尺,哪块地有没有金子,他们一眼就能看到。当年慈禧太后请他祖父到黑龙江漠河寻找过金矿,他的祖父为此发了财。他的父亲从祖父那里学来了识金的本领,被马步芳重金相聘,也财源滚滚。解放时,他家被土改复查,祖父被贫农团打死,缘由是剥削发家。其父虽然幸免,但屋中一切均被“复查”,留给他父亲的只有一身识金路的本事。这本事,“无产阶级”是不用的。他父亲被生产队长派去放羊。马长东亦随着父亲去放羊。在放羊间,他父亲把这识金断玉的本事一点点教给了他。马长东也算有心人,他都熟记于心,其父还告诉了他许多金矿埋藏丰富之处。“文化大革命”中,马长东父亲被折磨死了。马长东以为父亲传授他的本事无用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开始,他一人上山,但他的本事很快吸引住了周围的采金人。那些只有力气的采金者,都纷纷向他靠拢,他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核心,便组成了一个多人的采金队伍,他成了当然的首领。很快,他成了暴发户,腰缠百万贯。 我曾经听人说采金人(也做淘金人)有许多禁忌,为了在采访中注意,便问起他。他笑笑说:“禁忌很多,但采金人最忌的是玩女人,如果女人的阴风把金脉冲走了多那就不得了,这是我父生前再三叮嘱的。” 女人和金脉有何关联,我想从科学上论不出什么道理来,但采金人采到金子后,因玩女人把到手金子流出去,古往今来的例子不少,马长东的父辈的叮嘱,其道理大概来于此。而今,那些腰缠万贯,而做人的素质又很低下的人,有几个又不在女人身上花钱和费心思呢?我想,这个马长东尽管有其父之嘱,大概也不会脱离这轨道吧。 汽车缓缓的向上爬行。一群黑褐色的野驴从汽车前跑过,消失在另一座山头。这里的山,没有悬崖陡壁,缓缓的坡度,象馒头一样。这里的高山土壤为高山荒漠土,沙壤质和沙砾质。长着短小的驼绒藜、紫花针茅、小叶棘豆、芨芨草、飞冷蒿等。哈尔腾草原是个狭长型的河谷草原。哈尔腾河的走向,即草原的走向。 我向马长东问起识金的知识。马长东说:“沙里淘金这话你常听到吧?金子这五金之王,不喜欢群居,金矿有的和山沙结伴,有的同河沙相邻。人们要得到金子,就得到大量的沙子里去找。金子的形成有个过程,开始藏在坚硬的花岗岩里,和石英矿脉做‘邻居’,和铁、砷、锌等硫化物在-℃温度下,一齐结晶出来,生成了成块的金块。花岗岩不是金子的长久住处,当外界温度发生剧烈变化和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后,这些含金的矿石开始剧烈的风化,加上风雨的冲刷等作用而风化崩塌。矿石崩塌后变成无数的砂粒,金子被磨成极细的颗粒。这些砂粒和金砂混合在一起,经雨水和山洪冲到江河里、海洋里,沉积下来。这就是沙金为甚在河床内的原因。”他继续说:“据专家探测,黄金在地壳中全部的含量只占地壳含量的百万万分之五,在这茫茫大地 上要找它,确实不易。刚才我讲的是沙金的形成。除了沙金还有山金。沙金是被水流冲成碎块,带在松散的砂层里的。山金是在岩浆变冷后,剩下的温度最低、可以象水一样流动的岩浆填充到四周岩石的裂缝里而形成的。它们常常象鳞片、象粉末,或成块的夹在石英脉里。要想找到成块的金子那真是太难了,不过也有找到的,在澳州就发现过93.3公斤重的金块,人们为它取名为‘霍尔捷尔曼板’。在苏联乌拉尔也发现了重达36公斤的金块。” 马长东见我听得认真,又告诉我,金砂和其他砂粒相比要重得多,所以,总是沉积在水流速度突然变缓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流水只能冲走比较轻的沙粒,而让比较重的颗粒沉积下来。他还告诉我,说河底岩层的排列和沙金的储藏的多少也有关系,如果软硬不同的岩石一层层地和河流平行伸展,流水就能把所有的矿砂都顺着松散岩层所造成的凹槽里冲走;如果岩层排列的方向和水流恰恰垂直,它们就会象一排排的栏杆一样挡住所有的矿砂,使它们很快沉积下来形成数量丰富的矿藏。 我不想学采金,听起来朦朦胧胧。而马掌柜也决不会把他祖传找金的奥秘告诉我的。 五 在海拔多米的高度,我见到了采金者。这里为哈尔腾河谷上游,从雪峰顶上流下采的雪水,流经河谷时,冲走了石砂,留下了沙金,就是这些闪亮的东西,吸引着那成千上万的舍生忘死的人们。 我放眼望去。头顶,深蓝色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白云的距离那样近,仿佛伸手就能抓到似的。馒头形的山坡光秃秃的。那终年不化的雪山也清晰可见。在靠近河谷的山坡上,到处是帐篷。这帐篷真是五花八门,有用塑料搭的,有用防雨布搭的。塑料布颜色各异,红的、绿的、蓝的、白的,……把这山坡装扮的五颜六色。这些各式各样的帐篷绵延河谷,向上延伸,难以数计。 时值中午,太阳高照。河谷之中,那些采金人都赤条条的忙着。极强的紫外线给他们涂了一层油黑发亮的油彩,更加显示了这些雄性的阳刚之美。我问马掌柜:“他们为甚不愿穿衣服呀?” 马长东说:“也说不清为甚,天一热了,他们就把衣服扒光。” 我说:“这里也不算太热呀。” 小蔡解释说:“这里山谷海拔高,空气稀薄,采金是强体力劳动,人们容易疲劳,穿上衣服,多少影响血液循环。他们要节约每一分力气,用在采金上。” 倏然间,我脑子里涌出“竭尽全力”这个词。不禁感叹道:“这些采金人,真是竭尽全力了。” 马长东的汽车还要往上走,我和小蔡同他告别,因为这里已有采金人——小蔡说,有采金人的地方就有病人。果然,我们刚到一座帐篷(其实只是几块塑料布扯起的篷子)。那些赤身裸体的雄性们就围了过来。我仔细得打量他们,他们大都身材高大,为西北人典型的特征。那黑黝黝的皮肤既油亮又粗糙,看不出他们的实际年龄,看不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年龄大都在20~30岁间。从那身上隆起的一块块肌肉看,没有这样的体魄是淘不到金的。这里是体力和黄金的较量。那些体力不支的,都先后倒在了这里。命大的拉下山能活,命短的山谷就是葬身之地。 小蔡开始给采金人看病。我继续进行感性的观察。我连着进了几个帐篷,帐篷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脏,被子黑黑的,团成一团,羊皮铺在地上,也是脏兮兮的,锅碗瓢盆象是多日没洗过似的。而在帐篷的周围,到处都是大便,几乎是连成片。看到这些粪便,我忽然想到,人生长在社会上,总是要有各种法规约束才好,如果大家都乱来,那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象这里,大便快把人埋住了。 山上的空气太稀薄了,我大口地喘着气,只觉得手脚发软。而那些采金人都手脚不停地操作着。我惊叹他们的体力和意志。他们在进行着体力和意志的拼搏呀。 我来到了一个采金人面前。他操作的设备十分简陋,甚至可以说仍留存着原始采金的痕迹。两根木棍,支着一个搓衣板似的溜槽。槽上固定着“摇篮”,这就是淘金的坐床。他把矿砂放进摇篮后,用力筛动,并且不断的往里边舀水。这样,经过一次次的冲刷,那象麦皮般的黄色片片渐沉在溜槽底部。接着,他又把初选进的沙金,移到簸箕里边。在清水中不停的晃动。我看去,沙金在水中闪亮。 整个工序单调、枯燥。采金人见我看得认真,停了下来,给了我一支烟,点着后,我和他谈起采。他是甘肃永登人,27岁了,还没娶媳妇。在他家乡的农村,娶个媳妇要上万元。他家虽然承包了一些土地,但光靠粮食是不行的,他说粮食不值钱,只能填饱肚子。他要娶媳妇要盖房,这都要一大笔钱。他呢,没有别的本事,父母也是个跟土打交道的人,因而,他只有卖力气,就来到了这里。 我问他淘了多少金。他不说(后来我才知道淘金人有许多规矩,不告诉别人采金数也是规矩之一)。他告诉我,他是被一个叫马福的老板雇来的。马福为他提供各种方便,保护他的利益,为他提供技术咨询——后来我才了解到,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不搞“联合体”,不依靠“一方”,是难以立足的我忽然发现我脚下不远处摆着几块石头,石头上压着红布条儿,我不解地问他:“这是做什么呀?” 他告诉我,说这是“老爷府”,是采金人供的神,保祐采金人的平安,保祐采金人发财。老爷府到底是哪路神,他也说不清楚,反正采金人都这么供,他也这样供。 每个采金人都有着发财的愿望,但发财的并不是所有采金人。 在同采金人的闲谈中,我了解到,在这个雄性的世界,在这些进行繁重而又简单的劳动的人中,蕴藏着烈火,蕴藏着雷电。他们之中,往往因为一点点小事,也可以引起双方的大怒,脏话常挂嘴边,而抡铁锨的事时有发生。这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治保员,这里是充满野性的山谷。用采金人的话说,在这里“大打三、六、九,小打天天有”。那雄性天生具有的阳刚,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 我和采金人随便扯了扯,他们就给我讲了许多打架以至流血出人命的事。一次,两个采金团伙为争一块地盘打了起来,这些西北汉子,本来都火暴脾气,双方一抡铁锨,刹那间,所有的理智都没有了,在这山谷之中,只见铁锨飞舞,棍棒乒乓,一场酣战之后,一方以十数人负伤,两人死亡的代价输了。这些输的人也讲“义气”,输了就自动离开。这也是采金人特有的“品德”吧?因为这里是没人裁决胜负的。所以,胜败的标准很简单而又很明确,败了就退。 这种械斗还是有缘故而引起的,而还有许多的斗是无缘无故的。甚至彼此多看一眼,被看人张口就骂:“看甚?连你爹都不认的啦?”接着,就是彼此的拳打脚踢。 我在淘金点中转着,看着。在这荒凉的山谷中,到处都是弓着背劳作的人。那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清澈的水,经过他们脚下后,变得浑浊了,浑浊的水顺流而下。那一片片草场,被挖得破破烂烂,甚至掘地3尺。——我曾看过一份资料,资料中记载,在这高寒处的草,一撮要长十几年,上百年,可在采金人的铁锨下,瞬间即破坏了。至于山上的野驴、黄羊、野马、花貂……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成了这些采金雄性们的副产品。一片净土被污染了。 这天晚上,我和小蔡宿在了一个帐篷内,这是一个老板的帐篷,算是采金场中高级客房了。说它高级,不过帐篷是帆布搭成的。地上多铺了几张羊皮而已——老板们虽然有钱,但在这个充满野性山谷中,也无法用钱买享受。晚上,在漆黑的山谷中,亮着星星点点的火光。这是一些帐篷里点燃的蜡烛。但多数采金人都摸着黑,他们舍不得花钱买蜡烛。这些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广播、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每当天黑之后,便围在一起胡侃,侃的内容不固定,但多为“荤”话,用他们文雅的话说是“裤腰带下边的事”。当我在蜡烛下同几个采金人聊天时,我听到帐篷外不远处有粗犷的男声合唱,那嗓音七高八低。我不禁内心中感叹: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六 小蔡白天看了一天病,晚上忙到11点多才回来。他告诉我,山下一些大队的赤脚医生(人们的习惯称呼)听说这里死了人,也来了,可他们的药费高得惊人,吊个瓶要元。为了活命,那些采金的病者只好忍痛把采到手的金子都给了这些“赤医”。这样相比,小蔡在采金人中威望更高了,有的病人甚至给他磕头。说武警是好人,是菩萨。小蔡笑着对我说:“别听他们这会儿喊武警是菩萨,过卡子时就又骂街了。” 金钱的杠杆可以把人的面孔随意扭转。我在这脏兮兮、虱子成堆的破被子里睡了一夜。说是睡,实际上只是合了下眼,山的严重缺氧,使我的头昏昏的。虱子、跳蚤一起向我进攻——我忽然明白那些采金人为甚不穿衣服了,一定是虱子老咬他们。 第二天早起,我的嘴唇肿了,坐着还张口喘大气,双腿也不听使唤了。小蔡见我脸色不好。对我说:“你必须下山,这里可不能再呆了。” 我心里想:我还没有正式采访,怎么能刚上来就下去?心里这样想,嘴巴却张不开,耳朵也嗡嗡叫,头象裂开似的疼,而且一阵阵的恶心。刚好有辆汽车要下山。小蔡把汽车拦住,凭着他在采金人中的威望,把我安排在驾驶楼。尔后,汽车向山下驶去,我大口喘气,连眼也不愿睁了,一切都任凭小蔡的安排。 我在哈尔腾采金场只住了一夜,然而,这却是难忘的一夜。 (曾载入《北岳风》年第六期) 文字:作者提供 图片:作者提供 编辑:李国华 欢迎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j/9122.html
- 上一篇文章: 绘画大师的艺术工作室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