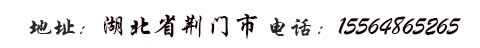李伯重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全
|
北京中医院治疗白癜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主持人语 年1月1日,北京大学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历史学系承担,意在沿着“海上丝路与郑和下西洋”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探讨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宗教,建立起系统扎实的基础研究体系,突破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学术界所把持、具有典型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及殖民/帝国主义色彩的历史解释模式,构建中国的世界历史学派。 本专栏刊登的三篇文章凭借详实史料,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丝绸之路的基本概念和解释体系重新作了考察和探讨,增加了新的历史解释维度,进一步证实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在形塑海上丝绸之路中不可或缺的贡献。 ——徐 健 作者简介 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摘要: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空范围中,中国的海外贸易也不例外。中国的海外贸易是世界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世界贸易的时空范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世界贸易在时间上呈现出四个大时期,引起了世界贸易的空间范围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这个大背景之中,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海外贸易;时空范围;全球史 不论对“丝绸之路”的性质、功能和作用有多少种看法,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丝绸之路”主要是贸易之路。既然是贸易之路,其主要功能必定是贸易。本文所讨论的,就是作为贸易之路的“丝绸之路”。 在许多论著中,“丝绸之路”被描绘为一条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洲际贸易大通道”,这条通道无远弗届,畅通无阻,世界各地商品通过这条大通道而实现无缝对接。无论什么时候,中国商品随时都可以通过这条通道,运销世界各地。然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大通道”并非真正的客观存在。要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空间和时间是首先要研究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维度,人类历史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演进历程。因此,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而任何过程都是通过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由于空间和时间问题是历史现象的基本条件,因此早在现代史学创立之初,兰克(LeopoldvonRanke)就明确指出:“这里涉及的事实,是一种准确的审核,要能够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离开了一定的时空范围,也就不成其为史学研究了。“丝绸之路”贸易既然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当然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因此,在“丝绸之路”研究中,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丝绸之路”贸易赖以发生的时空范围,以及这种范围所发生的变化。 一、全球史视野中的 世界贸易地理空间 贸易是一种经济活动,任何经济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即地理空间之中。然而这一点,过去学界却注意不够。年,克鲁格曼(PaulR.Krugman)在其《地理和贸易》一书的序言和开头部分写道: 作为国际经济学家,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所思考和写作的都和经济地理有关,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 国际贸易的分析事实上并没有利用从经济地理学和区位理论中得到的一些洞察。在我们的模型中,国家通常是一个没有大小的点,在国家内部,生产要素可以迅速、无成本地从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在表示国家之间的贸易时,通常也采用一种没有空间的方法:对所有可贸易的商品,运输成本是零。 然而,国际经济学家通常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国家既占有一定的空间,又是在一定的空间内存在的。这种倾向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忽略了这个事实。 地理空间的问题对国际贸易的研究至为关键。这是因为贸易的实质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商品的供求关系,而商品供求关系决定于参与贸易的各方之间对特定商品的供给和购买的能力。这种供需能力,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地理自然条件。 首先,商品的供需能力取决于地理环境。赫德森(MichaelHudson)指出:“商业似乎是以大自然本身为基础的。每个地区都以上帝赐予的独特资源为基础组织生产并形成了专业化。某些地区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贸易,如玻璃制造和金属制造;另一些地区生产稀有矿石、香料或葡萄酒。”换言之,一种商品的供给能力是一定的地理环境的产物。这种地理环境有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候条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这些对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贸易商品流向都有重大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则包括人口、民族、教育文化水平、语言、宗教信仰、历史、政治等。其中人口的构成(数量、素质、密度等)是决定一个地区市场规模的基本因素,其他因素对市场规模及贸易的地理方向、商品结构等也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其次,商品的供需能力也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一个地区参与贸易的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实力有密切的关系。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地区对市场提供的商品种类、品种、数量、质量,有着很大差异。而处于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及自身所拥有支付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也导致市场上商品结构及地理流向之间出现地区差异。 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贸易,就必须首先研究这种贸易的参与者的经济状况,了解它们对商品的偏好和供需能力。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必然是规模相对较大、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经济体,因为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有能力提供和购买较大数量的商品,从而保证贸易以可观的规模持续进行。 东半球有欧、亚、非三大洲。这三大洲,西方学界有人称之为“theAfro-Eurasianworld”或“theAfro-EurasianEcumene”,即“非—欧—亚世界”,本文从汉语习惯,称之为欧亚非地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这个地区是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世界贸易也集中在这个地区。 这个广大的地区由多个在各方面有巨大差异的部分组成。芬德利(RonaldFindlay)和奥罗克(KevinH.O’Rourke)综合考虑了地理、政治和文化特征,将其划分为七大区域,即西欧、东欧、北非和西南亚(伊斯兰世界)、中亚(或内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至于包括东西两半球在内的全世界,赖因哈德(WolfgangReinhard)等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把14世纪中期以前的世界分为五个不同的“世界”:大陆欧亚(ContinentalEurasia,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南亚和印度洋、东南亚和大洋洲、欧洲和大西洋世界。其中“大西洋世界”所涉及的欧、非、美三大洲(此处所说的非洲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彼此之间并无联系,美洲更是隔绝于欧亚非地区之外。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之间自古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后来逐渐发成了一种经常性的联系,一些学者称之为“世界体系”(theWorldSystem)。这种世界体系以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的关系为组织方式,亦即由一些核心区和边缘区组成,而核心区对其外的边缘区,在经济、文化上(有时还在政治上)都处于支配地位。各个核心区彼此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世界体系。 世界历史上的核心区中,有三个最为重要,即中国、印度和欧洲。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认为世界主要文明开始于公元前年前后的“轴心时代”(Axialage),此时出现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明,“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这三大文明之所以有持久的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三个地区具有相对高产和稳定的农业,其产出能够养活较大数量的定居人口,支持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为文明的持续提供物质基础。 一些“世界体系”学者对于历史上的“核心区”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看法。毕加德(PhilippeBeaujard)认为从公元1世纪到16世纪,欧亚非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有五个核心区(有时也有更多的核心区),即中国、印度、西亚、埃及和欧洲(包括地中海、葡萄牙和西北欧地区)。阿布-卢格霍德(JanetL.Abu-Lughod)则认为13—14世纪,一个从西北欧延伸到中国的国际贸易经济正在发展,将各地的商人和生产者纳入其中,而中东、印度和中国是核心。不论这些看法有何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都主要集中在欧亚非的一些“核心区”,这些地区之间的联系就是当时世界各地人类交往的主流。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核心区”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其经济规模较大,生产力水平较高,因此拥有提供较大数量的商品和获得较大数量的异地商品的能力。我认为大致来说,在16世纪之前,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应当是中国(主要是东部)、印度(主要是南部)和西欧(包括其控制下的东地中海地区)。这三个地区,至少从公元前两个世纪开始,就拥有当时数量最多的定居人口、规模较大而且较稳定的农业以及工商业,从而成为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具有大量和持久地生产和消费商品的能力,而且由于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自有一些独特的高价值产品。中国、印度和西欧三个主要经济“核心区”中,又以分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西欧最为重要。在“世界体系”开始形成的初期,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高的两大经济体。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沉寂,中国在唐代复兴,并自此以后在“世界体系”中一直拥有突出的地位。西欧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西部地区陷入长期混乱,但东部地区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仍然得以保持和平和稳定。拜占庭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国家,其人口数量超过中国、印度之外的任何国家。再后,从15世纪起,西欧的西部地区(意大利、伊比利亚、低地国家、法国、英国等)兴起,使得西欧重新获得罗马帝国曾有拥有的特殊地位。因此之故,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大部分时期中,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核心区”是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西欧。当年李希霍芬把“丝绸之路”的起止点定为中国和西欧而非中间的西亚,是很有见地的。 在中国、印度和西欧三大“核心区”之外,西亚(特别是波斯、两河流域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中亚(特别是河中地区)也都是古代的“发达”地区,但是与前三个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有限,经济规模较小,不稳定的游牧经济占有很大比重。因此相对于前三个地区而言,在经济上只能算是次一级的“核心区”。但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们能够在中国、印度和西欧之间经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因此它们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一种与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不相称的突出地位。世界主要的国际贸易也集中在这些地区之间。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很大改变。 上述这些核心区之间的联系如何呢?弗兰克(AndréGunderFrank)与吉尔斯(BarryK.Gills)等认为:在过去五千年的历史上,欧亚非大陆各地的交往有三大中心通道,这些通道在“世界体系”中起着特别突出的关键性的物资供应联系作用。这三大中心通道是:(1)尼罗河—红海通道(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由运河或陆路相连,与地中海相接,直通印度洋乃至更远的地方);(2)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湾通道(陆路经叙利亚与地中海沿岸相连,水路经奥龙特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到波斯湾,而后直通印度洋乃至更远的地方。这条中心通道还通过陆路与中亚相连);(3)爱琴海—黑海—中亚通道(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地中海与通往和来自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链接起来,而后经陆路通往印度和中国)。 芬德利与奥罗克认为在欧亚非主要地区之间,地中海和黑海的贸易传统上涉及伊斯兰世界以及西欧和东欧;印度洋将伊斯兰世界、东非、印度和东南亚连在一起;而南中国海则将中国与南洋群岛直接连在一起,并将中国与印度和伊斯兰世界间接连在一起。在公元1年以前的很长时期内,红海和波斯湾是东西方海上贸易路线中至关紧要的大门。陆路是可供选择的另一条路径,它搭建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系纽带,并通过中亚将中国与东西欧连在了一起。简言之,主要贸易路线为(1)地中海和黑海;(2)印度洋和南中国海;(3)穿过中亚由中国至欧洲的陆上贸易。 在上述主要通道和路线中,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洲际陆上通道,其起止地点是中国的长安(今西安)和西亚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这里要指出的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这条陆路并不是一条“商贸大通道”。在大多数时期,这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都只是区域性贸易。不仅如此,从贸易规模来看,这条丝绸之路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海上情况就不同了。弗兰克和吉尔斯所说的三大通道都与海洋有关,可以说都是海陆连接的通道。而芬德利和奥罗克所说的三条主要贸易路线中,两条是海路(黑海与地中海、印度洋与中国海)。因此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海路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看看这些海路所经过的海域。 毕加德和费(S.Fee)指出:在世界历史上,以地理因素和交流网为基础,亚洲和东非的海洋可以分为三大海域:中国海、东印度洋和西印度洋,西印度洋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波斯湾海域和红海海域。芬德利与奥罗克认为三大海域是地中海和黑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他们都没有谈及大西洋,这不并是有意无意的疏忽,而是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大西洋以及太平洋的主体部分都不是世界的主要海上活动发生的海域。只有它们的边缘部分(即位于太平洋的西部边缘的中国海海域和位于大西洋东部边缘的欧洲西北部的北海海域)才有相对较多一些的贸易等活动。 我认为15世纪末之前的东半球海上交通所涉及的主要海域,应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分:中国海、南洋(东南亚海域)、印度洋、地中海(以及附属的黑海)。很明显,这些海域相互联系的中心是印度洋。弗兰克和吉尔斯说在连接欧亚非的三大通道中,第一、二两条在物资供应方面所占有的地位更为重要,而这两条通道都是连接印度洋,或者说是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延伸。因此从海上贸易来说,印度洋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世界贸易的主要舞台。这一看法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毕加德明确指出:在古代的“世界体系”中,印度洋占有中心位置。这在地图上是一目了然的。中国海是太平洋的西部边缘,而欧洲北海位于大西洋的东部边缘。这两个大洋边缘的海域通过南洋和地中海与印度洋连接。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印度和西欧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核心区”。而在中国和西欧之间没有直达的海路,贸易交往必须经过印度洋。另一个主要经济“核心区”印度就位于印度洋,而中国和西欧都与印度有较为紧密的贸易关系。因此之故,印度洋也理所当然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舞台。 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这一传统格局被打破。欧洲人建立的“大西洋体系”,使大西洋海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区域之一。同时,欧洲人开辟了连接西欧和东亚的大西洋—印度洋—中国海和大西洋—太平洋—中国海的航线,连接了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到了此时,印度洋不再是世界海上贸易的中心。尽管从欧洲到东亚大多要经过印度洋,但除了印度,欧洲人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在沿岸各地建立据点,作中途补给以及安全保障之用,而欧洲和这些地方之间进行的贸易规模十分有限。 中国的海外贸易是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之中,上述世界贸易地理空间范围的变化,对中国的海外贸易具有巨大的影响。 二、全球史视野中的 世界贸易时间周期 世界贸易的地理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由于世界贸易是全球性的活动,深受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全球史学者康拉德(SebastianConrad)指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历史事件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即重视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事件,即使这些事件在地理上天各一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j/7545.html
- 上一篇文章: 杜特尔特的ldquo政治王朝rdq
- 下一篇文章: 年版小学16年级分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