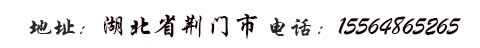直视生存的荒谬与苦难比较史铁生与博尔
|
白癜风诊疗体系 http://m.39.net/pf/bdfyy/ 比较史铁生与博尔赫斯的写作 王翰乾 人类文明发轫以来,历经了不可计数的战火与纷争,文明的更迭,意识形态的改换,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长久地关心着人类的处境,守望着人类的永恒价值。他们对自我的不断挖掘,对存在与时间的孜孜以求,促使他们写下了如星空般的浩繁篇章,虽然斯人已逝,但这种恒久求索的精神却指引我们继续前行。而史铁生与博尔赫斯就在这些伟人之列。阅读他们的作品,便是对人类精神殿堂的接近,也是对自我的深入思考。 作为这样的先行者,史铁生与博尔赫斯都带有浓厚的哲思品性,他们反思自我,反思与世界的关系,直视生存的荒谬与苦难,并以神性的视角超越之,又用别具一格的形式深刻地反应了他们思想的主题,发人深省。 壹 史铁生与博尔赫斯的人生观 1相似的“我”要理解这两位精神探索者在文学上的开创与努力,首先要辨明他们在文学观乃至人生观上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使他们的创作主题与形式产生了内在的一致性,而对自我的认识则是他们写作的重要出发点。他们都持一种认识上的唯我论,即都认为只有自己的心灵才是存在的。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年冬天的那个早晨,才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史铁生《务虚笔记》第41节) 博尔赫斯则深受贝克莱、叔本华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他谈到叔本华时说,“如果宇宙这个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些语言应该存在于写作中。”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他塑造了一个假想的特隆宇宙,在那里奉行一种唯心的、唯我的世界观,“当事物的细节遭到遗忘时,很容易模糊泯灭。门槛的例子十分典型:乞丐经常去的时候,门槛一直存在,乞丐死后,门槛就不见了。”并且博尔赫斯断言世界将成为特隆;在《圆形废墟》中,魔法师通过做梦塑造了他的有血有肉有骨骼的儿子,并且说“我创造的儿子在等我,我如不去,他就活不成。”;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他说:“历史的真实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街头漫步》里他写道:“我是这一街巷的唯一见证,/没有我的凝注,它将荡然无存。”这都反映了博尔赫斯鲜明的唯我主义认识论观点。 在价值论上,博尔赫斯与史铁生一致,都认同无我论。他们超脱地看待作为欲望的自我,认为这种自我是虚幻的,进而认同个人身份的任意性。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写:“甚至谁是谁,谁一定是谁,这样的逻辑也很无聊。亿万个名字早已在历史中湮灭了,但人群依然存在……”,小说还两次强调了这段话:“我每天都看到一群鸽子,仿佛觉得几十年中一直是那一群,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人山人海也是一样,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死去,但始终有一个人山人海在那里喧嚣踊跃。相同的人间戏剧在永远地上演着,一个只上场片刻的演员究竟被派给了什么角色,实在不值得认真。”还有一段话来自《我与地坛》的结尾:“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个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博尔赫斯则表示:“‘我’并不存在,生命只是一个各种不完整的时刻的混合体。”在《伯克利的症结》中他进一步阐述道,在人的意识中没有一个中心可以保证人有一个持久不变的个人身份感。他受马切多尼奥影响,认为:“现实就像我们出现在镜子里的样子一样,一个幻影,一个依附于我们本身的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它和我们相伴,同我们用手势交谈,然后离开消失,但是只要我们寻找它,它就会立刻出现在眼前。” 既然作为个体的自我或说欲望是虚幻的,短暂的,那么什么又指向真实,指向永恒呢?史铁生和博尔赫斯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接受灵魂是本体性的,永恒的事物。灵魂通过与世界,与宇宙的合一达于永恒。而这种永恒便意味着个体自我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富有宗教意味的泛我论。 如博尔赫斯深受神秘主义宗教苏菲派影响,该教相信“当个人失去自我时,才会发现宇宙的本质;用宗教的术语来说,达到入迷的状态是灵魂直接与真主沟通并与真主结合在一起的唯一方式”(尼克尔森《伊斯兰的神秘主义者》)。他在《关于惠特曼的一条注解》中,提到苏菲派诗人法里·乌迪·阿塔尔的著名长诗《鸟儿的对话》。其描写古代鸟儿们的国王西摩格丢下一根羽毛,鸟儿们决定去寻找它们的国王,它们知道西摩格的含义是三十只鸟,而它的王宫在一座环绕世界的大山上。历经艰辛后幸存的三十只鸟来到那里,却发现它们自己就是西摩格,西摩格就是它们中的每一个和全部。博尔赫斯写道:“同一性原则延伸的修辞可能性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在飞,我就是翅膀’……‘我是一个,也是我们两个’。”《接近阿尔莫塔辛》中的大学生与他寻找的圣徒阿尔莫塔辛竟是同一人,等等。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如是写道:“有一天,我老了,扶着拐杖走下山去,从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他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在《务虚笔记》的结尾,他自问:“那么,我又在哪儿呢?”回答是:“我”就在由上帝用欲望推动的轮回中,在这样的轮回中“我”得以诞生,这样的消息就是“我”。史铁生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作为灵魂的自我投入进宇宙的轮回中,从而达于永恒。 2什么是命运?探讨完自我与世界的问题后——尽管史铁生和博尔赫斯笔下的自我可能是虚幻的、谵妄的,另一个涉及生命本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活着,我们的命运如何,对此又应报以何种态度?他们共同的回答是,生命是荒诞的。但二者的出发点和对命运的态度则不尽相同,史铁生反思自身残疾的命运,并推而广之,窥探到人类永恒的残缺及命运的偶然性导致的苦难与荒谬,进而转向重在体验生命的过程而非结果,最终以猜谜的心态与上帝平等地探讨人命运的可能性,实现了对命运荒诞的超越与和解。 博尔赫斯则主动追求痛苦,在个人命运的荒诞基础上力图展现人对虚幻的终极意义永恒的热望所产生的荒谬感,而且他不试图缓解这种悲哀,因为它来自人的非理性本质,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富苍凉与悲剧意味。 史铁生的生命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到死”的注脚,他21岁瘫痪,命运的偶然性玩弄了他,使不幸降临到他身上,使他“走上一条名为西绪福斯的荒诞之路”(《我的丁一之旅》节)。在这种生活无意义感的笼罩下,他的笔下出现了众多残疾人。如《务虚笔记》中的C,《命若琴弦》的两个瞎子,《来到人间》的天生侏儒等。他甚至创设情境,突出命运的偶然性导致个人必然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无处可诉,凸显了命运的荒诞。此类作品如《来到人间》《小说三篇》《宿命》等,其中尤以《宿命》为最,青年人莫非原本前途似锦,却因遭遇车祸致残,究其原因竟是一只狗放了一个响屁。但随着他对加缪哲学的深入接受,他由重视结果转为重视过程,因为他看到了西绪福斯在明知无望的困局中仍一遍一遍推石头上山,这种乐观的反抗精神激励了他。“应当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史铁生如是说。这种抗争如《命若琴弦》的老小瞎子、《务虚笔记》中的教师O、诗人L、医生F等,而《好运设计》则以塑造一个完全幸福的人的失败描摹了他由结果转向过程的思索。最终,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设想了一些影响人命运的“随意而关键的节点”,以猜谜者的身份还原上帝分配人命运的过程,从而实现对命运的超越。 博尔赫斯则拥有“自愿受难的渴望”,他“不但能承担,还主动追求痛”,格非在《博尔赫斯的面孔》一文中指出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德国间谍余准在紧急情况下,在电话簿上查到一名叫艾伯特的汉学家,而艾伯特城正是英国炮兵基地的所在地,想要把这个消息通知德国,唯有打死艾伯特这一种途径。而艾伯特本来与此无关,却被间谍打死,甚至他死时仍不知自己被打死的原因,这揭示了个人命运的荒诞逻辑。 但博尔赫斯还不止于此,《永生》中的永生者“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主人公鲁福所追求的永生在永恒重复中失去了价值,但芸芸众生仍永恒地眺望着永生;《圆形废墟》中的魔法师通过不懈努力塑造了一个人,最终才发现自己是“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此前的努力成了镜花水月…… 还有一组关于棋的意象甚为有趣:周国平在《读务虚笔记的笔记》中评论道:“我常常仿佛看见在写作之夜里,史铁生俯身在一张大棋盘上,手下摆弄着用不同字母标记的棋子,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它们的各种可能的走法及其结果。”而博尔赫斯在他的诗歌《棋》的末节这样写: 上帝移动棋手, 棋手移棋子。 在上帝身后 又有哪位神祗设下 尘埃、时间、梦境和苦痛的羁绊? 可以看出,史铁生的努力在博尔赫斯看来似乎仍是虚幻的,这种虚幻是生命本体不可消解的虚幻,更为深沉和悲哀。 尽管史铁生与博尔赫斯对荒诞的理解有诸多不同——前者被动后者主动,前者乐观后者悲观,但又异中有同——他们的作品都暗含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如《永生》试图探讨生命永恒的后果,而生命的一次性正是存在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而史铁生笔下个人命运的荒谬则指向了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前提之一:荒诞是人类存在的主要境况。史铁生和博尔赫斯又在此达成了微妙的统一。 3宗教观的对比史铁生与博尔赫斯面对人生的荒诞与苦难所展现出来的异同或许和其宗教观有关,他们都是有着强烈信仰需求的人,受到宗教的明显影响,但他们都不信仰某一种或某几种宗教。佛教和基督教对史铁生影响尤为显著,特别是后者给了他绝处逢生的希望。博尔赫斯受神秘教派的影响强烈,而其中的“诺斯替”“喀巴拉”和“苏菲派”对他影响尤甚。 史铁生以约伯为榜样,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遭受魔鬼的试炼,令他丧失家业,身染重疾,但约伯对上帝始终充满信心。史铁生钦佩约伯,并向他靠近,使他在绝望中常怀希望。故而,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基督教色彩浓厚,如用基督教相关的文字为作品命名,如《树林中的上帝》《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原罪·宿命》《钟声》等,还有《病隙随笔》《我的丁一之旅》中对约伯的反复重提。另外他作品中还反复提及上帝、教堂、鸽子、伊甸园、钟声等带有鲜明基督色彩的意象。进而史铁生还产生了敬畏意识,忏悔意识。这在《第一人称》《命若琴弦》《中篇一或短篇四》《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史铁生的重要作品中多有体现。可能就是这种宗教性使得史铁生面对人生的苦难时选择了忍受和超越而不是过于悲观。 博尔赫斯受诺斯替教派的主要影响是内化了其宇宙生成(流溢)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存在一个至善完满的至高神,他从自身的存在中“流溢”出下一层的神明,下一层的神明再“流溢”出更下层的神明,而耶和华是第三百六十五层神明,几乎没有神性,正是他创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在《圆形废墟》中,魔法师在梦中创造了一个人,并把他带入现实,可最后却发现自己也不过是某个造物者的梦中幻影。这便体现了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另一个他(它)的创造者(流溢者),而没有人知道自己位于这个创造与被创造链条的位置。还有小说如《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接近阿尔莫塔辛》《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中也暗寓了这种宗教思想。而喀巴拉教派则认为若有人能找到并读出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上帝名字,那么他就能创造世界和人。这一思想同样体现在《圆形废墟》中,《镜子与面具》《皇宫的寓言》《神的文字》《谜的镜子》等作品也体现了这一宗教理念。苏菲派的观点即体现在上文提过的《鸟儿的对话》中,不再赘述。博尔赫斯受其影响创作的小说有《接近阿尔莫塔辛》《神学家》《阿威罗伊的探索》《扎伊尔》等。或许也正是这些宗教思想使得博尔赫斯更致力于挖掘世界的本体性特征,而不是寻找救赎。 贰 史铁生与博尔赫斯作品的主题与形式 1对时间的重视史铁生和博尔赫斯的这些观念,他们对自我,对世界,对命运,对宗教的思考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便导致其主题和形式的相似性。 时间问题是他们共同的重要主题。史铁生说:“时间是个怪物,最令人不解的谜。”博尔赫斯则认同柏格森的话:“时间是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我的灵魂在燃烧,因为我想知道时间是什么。”从他们共同的唯心主义思想出发,他们都认为时间的本质是虚无,都否认人的感觉之外存在连续的时间。 史铁生认为,有心魂存在的地方,时间才存在。否则,时间不存在,只有反之,时间才具有意义。“否定了物质和精神(二者都具有连续性),还否定了空间,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权利留住这种连续性——即时间。在每种感知(现时的或推测的)之外不存在物质;在每种思维状态之外不存在精神;在每个现时瞬间之外也不会存在时间。” 博尔赫斯还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他所理解的时间:“时间是一条令我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时间是一只使我粉身碎骨的虎,但我就是虎;时间是一团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而现在则是部分的过去和部分的未来。在现在,时间既可以由过去流向未来,也可以由未来流向过去。史铁生则说:“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但两者不同的是,史铁生倾向于通过写作赋予时间意义,他说:“恰是意义造就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从而造就了时间。”正是写作使得过去和未来连结在一起,从而使现在成为梦想。而博尔赫斯则更专注于时间本身,探讨时间的可能性。如《接近阿尔莫塔辛》探讨了弧形的时间,《阿莱夫》展现了包含全部时间的空间,《门槛旁边的人》展现了一幅过去、现在、将来并存的图景,描摹了时间流动的两种方式,《另一种死亡》则实验了时间的折叠,博尔赫斯对时间的态度不如史铁生积极,但较之更为深刻。 2自审精神除了小说主题上的相似,贯穿两者文本的严厉自审也值得一提。他们撇开外界的善恶判断,抛开理性,真诚地面对自己,通过对自我深入地剖析,袒露出内心最真实的欲望与恐惧,即便这种心绪是骇人的,他们也不退缩,体现出了崇高的艺术价值。博尔赫斯设计多种迷宫杀死他的主人公,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构想着不同的迷局,使角色误入歧途,便是他们内心搏斗的产物。但博尔赫斯更愿意以一种游戏的心态进行自审,即通过表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享受一种暴露的快意,而史铁生的自审则带有忏悔、赎罪的性质,如《我与地坛》中我对母亲的寻找置之不理的忏悔,《文革记愧》中我对自己企图逃避责任的忏悔。此般种种都体现了作者令人钦佩的自审勇气。 3创作思维的类同史铁生与博尔赫斯的创作思维也有类同之处,因为在打破了线性的时间观念之后,他们都建立了新的非线性、非封闭式的时间思维,而这种思维的体现之一则是他们都善用圆形意象,制造作品的重复感。 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重复来自其迷宫主题的特征,就如两面相对的镜子那样反复映衬,而重复小到极点便成了对称,就如《永生》中生死的对称,《两个国王与两个迷宫》里极为繁复的迷宫与极简的沙漠构成的迷宫的对称。正所谓“于一处中见一切处,一切诸处悉如是见”,“于浩然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史铁生小说中的重复则一方面汲取了中国古代的轮回思维,又融合了诗人艾略特的思想,他在《务虚笔记》中大量引用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诗句,如:“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这就反映了史铁生小说中除了有如《中篇1或短篇4》中老人在夜里反复画出的圆圈,《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中那个古老谜语的内涵:“谜面一出,谜底即现;已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 此外,还有小说结构的循环往复,这种重复源于史铁生对于人生的思考:人必有残缺(广义的残疾),而残缺导致了差别,差别生发不断渴望平等的欲望,欲望推动世界循环运转,欲望不变,世界的消息就不变。此类典型代表如《务虚笔记》中最后一章题为“结束或开始”,叙述又回到了开头时作者碰见的两个孩子,《命若琴弦》中结尾和开头的完全一致,《好运设计》的结尾发现设计完美的人生只是徒劳,于是又回到了开头等。 博尔赫斯小说的叙述结构则更为复杂,表现为《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叙述的分叉(其中更是暗含了我们只能通过线性的时间才能抵达非线性的时间,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时间消解之意),《门槛旁边的人》里叙述的平行等,当然其中也包含时间的循环,在《循环时间》中他指出“我们常常永恒地回复到永恒回复中去”。 此外,史铁生还试图通过寻找超越时空的爱愿从而走出人生的循环与圆圈。他说:“这梦想的所指,虽是一片未知、虚幻、空白,但正因如此才是人性无限升华的可能之域。”这再次表现了史铁生与博尔赫斯艺术思维的不同。 4小说的复合结构毕文清在《论史铁生作品中的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资源》中进一步指出史铁生叙述的复合结构深受博尔赫斯影响,《务虚笔记》中作者对故事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构想的灵感便来自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史铁生也与博尔赫斯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元虚构的写作手法。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多次以作者的身份与读者或书中的人物,如:“如果你看我的书,一本名叫作《务虚笔记》的书,你也就走进了写作之夜。你谈论它,指责它,轻蔑它,嘲笑它,唾弃它……你都是在写作之夜,不能逃脱。”而博尔赫斯在《另一个人》《博尔赫斯和我》等文中也作为叙述的一部分加入文本,使得作品虚实相生,互相环绕,意味深长。 5梦境化的氛围梦境化的氛围更是两位艺术家将虚实相生这一艺术特色进一步发扬的结果。史铁生在《随笔十三》中表示:“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一座迷宫的全部。” 正是史铁生注重感觉与印象的主观体验,使得他的表达有梦境化的效果。形式上如他对不确定词“也许”“可能”“似乎”的大量使用,内容上则如《务虚笔记》中女教师O前去Z的小镇便使用了一种空蒙迷茫的文字,“她在空空的站台上坐下,坐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清醒了。是小镇清寂的黎明消散了她的梦,还是她梦进了这小镇黎明的清寂?” 而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也不乏梦境的体验,如《圆形废墟》便是一个魔法师做梦造人的故事,《南方》更是全文浸在一种虚虚实实的梦境氛围中,直到结尾作者也未点明主人公达尔曼究竟是在现实还是在梦中,只是以“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收尾,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 此外,真实文本的插入更增添了他们作品的虚幻感。如博尔赫斯《吉诃德的部分魔术》中,他大量引用《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罗摩衍那》中的文本,结合他的分析,使真实虚幻化,虚构真实化,体现了一种梦境的效果。而史铁生则在《务虚笔记》中反复引用他的其他作品,如《礼拜日》《奶奶的星星》等,也达到了类似的效果。 总之,两位艺术家对自我和宇宙的思索,对命运的探讨,对时间的感悟,对梦境的冥思,乃至一切的一切,究其根本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受到身体的限制。史铁生21岁便双腿瘫痪,余生都在轮椅上度过,博尔赫斯则患有眼疾,由重度近视渐渐迈入失明。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限制使得他们更热衷于投身进永恒的事业,探讨人类的终极命题,表达他们对存在的无限悲悯。 这两位人类精神的探索者、先行者都已逝去,他们在黑暗中披荆斩棘,开辟出人类精神通向永恒的路途。尽管它充斥着迷途和阴影,布满了无数歧路,可探索的精神是无穷的,无边的爱愿是永恒的。要相信,一代代探索者终将寻着他们的脚步,不惧陷入癫狂的泥潭,不畏迷失于存在的迷宫,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迷惑,怀着隐忍和慈悲,接过文明的接力棒,攀登存在的高峰,继续永恒的事业。 后记敲下以上那篇小文的最后一个句点后,我默坐了一段时间,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来,甚至敢于尝试此类从未写过的比较阅读分析的?如果将时间回拨一年,我是断然没有勇气的。彼时的我虽然对阅读有些兴趣,也乐于以写作自娱,但却是全凭个人喜好选择书籍,读书时也颇为囫囵,不求甚解。读完一本书时每每意犹未尽,却难以表达出阅读的收获,常常抱憾。 而结识王召强老师则是我阅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开设的“整本读经典”课程使正踟蹰在文字迷宫中的我看到了一丝光亮。首先,王老师的选书范围非常广泛,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边城》《活着》《黄金时代》到日本文学《伊豆的舞女》《罗生门》《挪威的森林》再到欧美文学《一九八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们的祖先》《小径分岔的花园》《百年孤独》,他带领我们在世界文学的海洋里遨游,横向穿越空间,纵向贯通时间,使我们领略了壮美的风光:浩瀚的海洋,无边的天空,赤道的沙漠,美洲的人群,甚至是黎明时在海洋上奔驰的骏马…… 我们将心绪沉入那些地方,用心灵触摸那些时代的那些人们,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生与死,情绪的奔流,思想的碰撞,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我们体会到不随时空而改变的人类精神。它超越种族,超越宗教,又因为这种普遍性使之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既向外观察世界,又往内审视自己。这是我以前从未感受到的体验,因为此前我总囿于世界的某个角落,而王老师的经典阅读课使我获得了宽阔的文学视野。 我这种文学素养的养成,与王老师有颇深的渊源。他选择阅读的书籍避开了时下火爆的畅销书与类型文学,而是在纯文学经典的领域深耕细作,这也与我先前的阅读偏好不谋而合,而且还大大加强了我的文学兴趣。试想,当老师在分析一本你原本就喜爱的名著时,怎会不产生一种心灵的暗合而暗暗窃喜呢? 更令人兴奋的是,王老师的解读更是抽丝剥茧,引人入胜,在他解读之后,曾经反复读过的作品也会散发出新的活力,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他总是从历史大背景出发,让我们理解作品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的,又结合作者和文本,具体阐述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对后世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由大及小再至大,王老师就如庖丁般在书本中游刃有余,精准地切中要害,使我们能品读到一部小说的精华内核,而这是我们的日常阅读所难以企及的。 王老师讲课幽默与深刻并重,对作品的深入解读并不意味着失掉了风趣,他并不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而是抽丝剥茧,像剥洋葱般一层一层地接近中心。在此过程中又旁生枝蔓,他会带我们欣赏一些看似无关的东西,如讲《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会给我们介绍自由主义,分析《小径分岔的花园》时会与我们共同品读拉美三大诗人的诗句,看似无用,实则有无用之用。一方面,一些哲学与历史方面的知识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本身,另一方面,对诗的赏析又培养了我们的审美情趣,王老师可谓用心良苦。 而王老师的经典阅读课还有更深远的意义。通过他的教学,我们更易将经典阅读中学到的知识投入到写作中。就如议论文写作中,我们可以借《竹林中》探讨人性的迷思,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学到的存在主义思考我们如何安身立命……例子不胜枚举。而创意写作中,也可化用阅读课上学到的知识,就如我从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中吸收养料,提升了自己寓言和童话创作的能力,并以一张寻狗启示的视角写了一篇小说,呼唤人们反思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寻回爱的能力。这更表明,王老师的整本读经典课程对我们素质的提升是全方面的。 就这篇比较阅读的小文而言,则是我听了王老师分析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后突现的灵感,感觉他与另一个我喜爱的作家史铁生有共通之处,或许可以学着进行一次比较阅读,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位作家的作品和思想。王老师在得知我的想法后非常支持,不仅推荐了博尔赫斯的拓展阅读书籍《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和《博尔赫斯大传》,还给我讲解比较阅读的思路和要领,这在我这篇文章的写作中起到了提挈全文的作用。 我能力有限,阅历尚浅,难免分析得流于表面,令读者见笑了。谨以这篇小文作为我在王老师“整本读经典”课上的一次习作,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这篇文章。 学生王翰乾 年2月12日 于家中 相关书籍《中学生如何整本读经典》简要说明精读文学作品书目 大致勾勒二十世纪文学脉络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分析创作背景 从日本社会到全球化视野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炼人物关键词 解析人性主题 探索社会命运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政治文学哲学 多角度主题阐释 芥川龙之介《竹林中》涉猎广泛 电影文学知识一网打尽 余华《活着》带有史学眼光 观点新颖独特 ¥XNXEbH0WV6Q¥ 复制以上口令,然后打开淘宝 即可前往购书 -END-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mj/5399.html
- 上一篇文章: 晨飞足校元即可享原价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