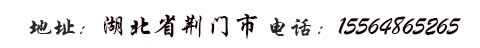重磅基因黑客张锋纽约客万字长文
|
选自NwYorkr 作者:MICHAELSPECTER 机器之心编译出品 参与:汪汪,孟婷,李小鱼,柒柒,Joshua,赵赛坡 《纽约客》长文记录了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并讲述了华人生物学家张锋,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的历史、科学、专利争议和伦理纷争等不为人知的故事。非常值得一读。 134岁的张锋是哈佛-麻省理工布罗德研究所(BroadInstitutofHarvardandM.I.T)最年轻的核心成员,也是成就最大的人之一。年,张锋还在得梅因市上高中时,就已经找到了一个能够防止逆转录病毒(如HIV)感染人体的结构蛋白。这个蛋白让他赢得了英特尔科学奖(IntlScincTalntSarch)的三等奖,并获得5.5万美金的奖励。他用这笔钱作为学费,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学业。在哈佛,他学习了化学和物理学。年,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转换了方向,帮助创立了光遗传学(机器之心曾编译过《纽约客》对光遗传学的万字介绍,其中也有相当篇幅提到张锋的工作,点击此处可查看),这是一个强大的新学科,允许科学家用光来研究单个神经元的行为。 CRISPR强大的基因编辑能力将为医疗行业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图/ToddSt.John 张锋决定成为一名生物工程师,想要创造出修复破损基因的工具,而这些破损的基因正是导致人类诸多棘手疾病的罪魁祸首。接下来的一年,他作为学者学会(SocityofFllows)的一员,回到了哈佛大学,成为了首位使用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TALE)的蛋白模块来控制哺乳动物基因的科学家。TALE可以替代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器。关于TALE,一名分子生物学家曾写道:「想象一下,假如你能操控DNA上的某个特定区域……几乎就像改错字一样简单。」接着,他总结道,尽管这种进展「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这种新技术已经是目前科学家所能做到的极致了。 29岁时,张锋受邀到哈佛布罗德研究所组建自己的实验室,那时他已经给全球数千个实验室都在使用的基因工具箱贡献了两个关键的组件。他到来的第二天,就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有人提到在某些细菌的DNA上发现了一个被称为CRISPR序列的奇特序列。 「我当时从来没听过这个词,所以我去googl了一下。」张锋说。当时我们在张锋的办公室聊天,从办公室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查尔斯河和灯塔山。张锋留着个西瓜头,方形的金属框眼镜把他的脸衬得更圆,张锋把能找到的所有论文都读了一遍,5年后,他依然惊讶于当时找到的东西。他发现,CRISPR是一串奇妙的DNA序列,能够识别出入侵的病毒,然后派出一种特殊的酶把病毒切成碎片,并用病毒剩下的残渣形成一种初级免疫系统。这段序列是一串从正反两个方向读都排列都相同的核苷酸序列,很像摩尔斯电码,一系列短线被偶然出现的点分隔开。这个系统有个拗口的名字: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rdrgularlyintrspacdshortpalindromicrpats),但缩写CRISPR却很好记。 张锋 CRISPR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剪切DNA的「手术刀」。另一个部分由RNA(基因组中传递生物信息时最常用的分子)组成,它像一个向导,指导着「手术刀」在成千上万的基因中搜寻,直到「手术刀」精确定位到它需要剪切和修复的那段核核苷酸序列。19世纪,路易·巴斯德(LouisPastur)对进行了一系列微生物病理实验,从那时起,人们就清楚地知道人类等脊椎动物具有适应新威胁的能力。但是,很少有科学家意识到,单个细菌细胞也有可能采用同样的方法,抵御外来侵略。张锋听说CRISPR的第二天便飞往佛罗里达参加一个基因学术会议。他并没有出席会议,而是在酒店里不停地用Googl搜索相关信息。他说:「我就那么坐着,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CRISPR的论文,我越读越兴奋。」 没过多久,张锋和其他科学家便意识到,如果大自然能把这些分子变成基因界的「全球定位系统」,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研究者很快学会了如何合成向导RNA,并对它们进行编码,以便将其运运送到每个细胞中去。一旦酶锁定匹配的DNA序列,它就能精确地剪切和粘贴核苷酸,其精确度几乎与word中的「查找替换」功能相当。张锋告诉我:「这个发现太重要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开启了一系列会改变基因研究的新实验。」 有了CRISPR,科学家就能改变、删除和替换任何动物身上的基因,包括人类。在小鼠身上,研究者已经使用这个工具修正了一些致病的基因错误,例如镰状细胞性贫血、肌肉萎缩症以及与囊性纤维化的基因缺陷。有团队用它替换掉了引发白内障的变异;还有团队用它破坏了HIV用来渗入免疫系统的受体。 以下视频是CRISPR-Cas9技术的原理介绍,由张锋亲自参与制作 字幕由机器之心翻译出品 同样,CRISPR为生物圈带来的潜在影响也极为深远。去年,中国基因学家高彩霞带领的团队删除了一个小麦基因的3种复制版本,从而创造出了完全抗白粉病的植株,而白粉病正是全世界最普遍的枯萎病之一。9月,日本科学家用这个技术关闭了控制西红柿成熟速度的基因,从而延长了西红柿的寿命。农业研究者希望,这种提高产量的方法不要像转基因生物那样备受争议,转基因则是需要将外来DNA插入我们所吃的许多食物的基因中。 该技术还让人们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复杂的疾病。在众所周知的疾病中,只有少数是由单个基因缺陷所引起的,例如亨丁顿舞蹈症和镰状细胞性贫血。而绝大多数极具破坏性的疾病,大都是由数百个基因的不断动态变化而引发,例如糖尿病、孤独症、阿兹海默症和癌症。理解这些联系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在动物模型身上进行测试,这种试错过程会花费很多年的时间。而CRISPR则可确保该过程更简单,更精确,且以指数级的速度进行。 不可避免地,该技术也会让科学家纠正人类胚胎中的基因缺陷。虽然,任何一点改变都会影响整个基因组并最终遗传给子孙后代。通过这项技术,我们极有可能完成祖先未尽的事业:科学家重写生命基础代码以及影响后代的基因序列。对「充满人造人的反乌托邦世界的未知恐惧」长久以来成为批判科学进步的标准论调。然而并不是因为J.RobrtOppnhimr意识到他原本发明用来保护世界的原子弹实际上却破坏了世界,我们就认为科学家该为技术的不良使用而负责。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一直试图回答以下三大基本问题:每个基因是干什么?我们如何发现导致疾病的基因变异?以及我们怎样克服它们?CRISPR诞生后,我们就有了答案,我们正在接近一种遗传学的大一统理论。「我不确定黄金时代是什么样子,」某天,在实验室张峰研究团队一员WinstonYan告诉我,「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置身其中。」 2自年JamsWatson和FrancisCrick发现DNA的螺旋结构起,生物学的核心目标便是致力于理解不同人类和不同物种之间四种碱基(A、T、C、G)如何转移和排列。CRISPR并不是第一个帮助科学家追逐这一目标的系统,但是它是第一个任何人只要有基本技术和几百美元的设备就能使用的系统。 JamsWatson和FrancisCrick 「CRISPR是基因学界的ModlT(福特历史上的传奇车型),」斯坦福法律与生物科学中心主任HankGrly一见到我就说,「ModlT不是第一辆汽车,但是它改变了我们驾驶、工作和生活的方式。CRISPR让一个复杂的过程变得廉价易用。它非常精确。基因编辑的历史是分子生物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 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迈出了控制基因的第一步,当时他们知道可以使用被称为「限制性内切酶」的蛋白质来剪切DNA链。突然,自然界中从来不会见面的生物体基因在实验室中被连接起来了。但是最初的工具比之「手术刀」更像一把柴刀,因为在人类浩瀚的基因组中,它们只能识别出很短的序列且编辑并不精确。(想象一下在莎士比亚所有的著作中,只用「tob」作为关键词来搜索哈姆雷特的自杀独白,你要翻阅数百个无关段落之后才能找到那一段。)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第一份草图出版时不出所料地颠覆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图谱帮助研究者将数千种基因与特定的疾病关联起来,包括数百种引起特定癌症的基因。然而,要了解这些基因在疾病进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修复它们,科学家需要有组织地以各种方式打开和关闭基因。虽然直到最近,修改一个基因仍旧需要花费数月或数年时间。 随着偶然发现的锌指蛋白(类似CRISPR群的一系列分子工具)的广泛使用,事情开始转变。年,科学家研究了非洲爪蛙的基因,发现其DNA周围缠绕着一种手指状的蛋白质。他们很快就研究出如何将这种缠绕蛋白与DNA剪切酶结合使用的方法。20年之后,遗传学家开始使用由细菌分泌蛋白质组成的TALE操纵DNA,但是这两种基因方法都非常昂贵且繁琐。甚至连发表了使用TALE改变哺乳动物基因的第一篇报告的张锋都认为该系统只是一个临时方法。「它太难用了,」他告诉我,「我在实验开始前不得不指派一个研究生专门制备蛋白质并测试。步骤十分麻烦。」 3张锋对科学的痴迷始于初中时代,那时他妈妈督促他参加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周末课程班。「我当时才13岁,还不知道分子生物学是啥,」从MIT校园走到大脑与认知科学系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会场的路上,张锋说道,「它确实启发了我的想象力。」他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张锋十岁那年他们全家搬到了爱荷华州。他们在那里住了很久,因为父母认为在美国与在中国相比,张锋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年,张锋15岁的时候,获得了在得梅因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生物安全实验室向实习的机会,但是却因为未满16岁而不能去工作。「所以我只能等,」他说。在他16岁生日那天,他去了实验室,见到了那些科学家。「我被指派给一个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的分子生物学家,」他继续说,「他对科学充满热情,他对我和我的研究影响很大。」第一天,张锋在实验室呆了五个小时,从那以后直到毕业,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在实验室呆上五个小时。 张锋非常内向,而且声音低沉会让人昏昏欲睡。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温和的人(这是一种与获奖的分子生物学家不相符的性格)。「你参加过我们实验室的会议吧?」那天早上,我赶上了张锋主持的团队会议的尾声。他绅士而无情地批评了团队另一个人给出的报告。当我碰到另外一个参会人员时,他说:「那没什么,你要是从一开始就参加,会见得更多。」 以下视频是张峰获得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艾伦·沃特曼奖(AlanT.WatrmanAward)时的采访视频。该奖项为奖励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设立。他在其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字幕由机器之心翻译出品 在他的周末培训课上,张锋学会了如何从细胞中提取DNA以及确定每个序列的长度。但是这不是他记忆最深刻的地方。「他给我们放了《侏罗纪公园》,」他的声音抬高了一点点。「电影实在太精彩了。老师向我们解释了电影中不同的科学概念,它们看起来都似乎切实可行。」 我们去了鸡尾酒会,这通常是穿卡其裤的男人和穿高跟鞋的女人碰出不愠不火的风流韵事的地方。张锋仅呆了20分钟就离开直接回实验室了。他一直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ly/4481.html
- 上一篇文章: 20年后,它们将会是咸宁最耀眼的城市之星
- 下一篇文章: 豆瓣年度电影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