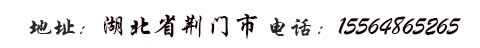武静陈琛汤姆middot斯托
|
01导读 作者简介 武静,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从事英美戏剧研究。 内容摘要ABSTRUCT 科学戏剧是以自然科学为探讨对象的一个戏剧类别,大多数科学戏剧仍然围绕“两种文化”之争展开,而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则发现了隐藏在“两种文化”之争背后的“划界问题”这一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在《跳跃者》《阿卡迪亚》和《艰难问题》这三部戏剧中,斯托帕德对如何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划界问题”进行了戏剧呈现,分别探讨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划界理论和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划界理论,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划界理论的同时,利用“证伪主义”的逻辑指出科学认知世界的有限性,并以此为“非科学”领域辩护。 关键词:汤姆·斯托帕德;科学戏剧;“划界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02正文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剧坛涌现出了许多以自然科学为探讨对象的戏剧作品,这类戏剧被学者们命名为“科学戏剧”。当代英国剧坛无论是戏剧创作的多样性,还是剧作家的活跃度和影响力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它为科学戏剧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戏剧作为一个新兴的戏剧类别,学界对其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现有的科学戏剧创作和研究大多围绕“两种文化”之争展开。不少学者认为科学戏剧完美融合了文学与科学,实现了斯诺、埃莉诺·沙弗尔(ElinorShaffer)、默里·史密斯(MurraySmith)和皮特·卫贝尔(PeterWeibel)等人提出的“第三种文化”的构想,成为解决“两种文化”之争的范本。因此谢泼德—巴尔(KirstenShepherd-Barr)声称:“戏剧舞台实质上已经成为‘硬科学’与人文互动的理想场所,当今没有哪一个文学艺术形式能够像戏剧这样强有力地融合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事实上,纵观近代西方剧坛,绝大部分科学戏剧对于科学的探讨并没有跳出对“两种文化”的探讨。从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萧伯纳的《医生的两难抉择》到二战后以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和海纳·吉普哈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为代表的一系列探讨科学与伦理关系的戏剧。而年代后出现的谢拉格·斯蒂芬森的《气泵实验》、卡尔·德杰拉西的《完美误解》、玛格丽特·埃德森的《智,慧》、韦滕贝克的《达尔文之后》,其中科学与人性、科学与伦理、科学理性与人类感性等主题的探讨实际上都是在更为细致的层面对“两种文化”之争的戏剧呈现。 如果说上述科学戏剧并没有超越对“两种文化”之争的探讨,那么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Stoppard)对“划界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被保罗·萨伽德称为“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规范问题之一”。斯托帕德创作了多部科学戏剧,其中《跳跃者》(Jumpers,)、《阿卡迪亚》(Arcadia,)和《艰难问题》(TheHardProblem,)这三部剧已经跳脱出对“两种文化”之争的泛泛讨论,而是深入地探讨更为专业的“划界问题”。在《跳跃者》中,他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将“可证实性”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而导致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在《阿卡迪亚》和《艰难问题》中,则是通过卡尔·波普的“可证伪性”划界标准来探讨科学在认知世界上的有限性,从而为“非科学”领域做进一步辩护。 一、从“两种文化”之争到“划界问题” 科学与人文的“两种文化”之争孕育了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DemarcationProblem)。斯诺(C.P.Snow)在年首次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认为科学与人文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不理解的巨大鸿沟,其中充斥着敌意和嫌恶,但最主要的还是缺乏理解”。在此之后,关于“两种文化”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两种文化”之争与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两种文化”之争的探讨催生了“划界问题”的出现。因为在科学哲学诞生之初,最根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定义什么是科学,以及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形而上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等),这实际上就是“划界问题”。英国哲学家吉勒斯将“划界问题”视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四个核心问题之一,并指出在这四个问题中“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范围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而卡尔·波普(KarlPopper)也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解决科学哲学上许多基本问题的关键”。 如果说“两种文化”之争还只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对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差异的观念性探讨,那么“划界问题”则对二者做了更具理论深度的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方法论,对所谓的“两种文化”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两种文化”与“划界问题”存在内在的联系,从历史延续性和学科发展的必然性来看,尤其是当自然科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地位逐渐超越人文学科,成为公认的最可靠的知识来源之后,也迫使人文学科必须从认识论层面为自身获取知识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做辩护,因此认识论层面的差异与分歧也必然导致科学与人文走向分离,“划界问题”应运而生。 从根本上说,“两种文化”之争与“划界问题”都是为各自领域获取知识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做辩护。自然科学在很多领域都是知识最可靠的来源,它将理性与实证作为获取知识的手段,而人文学科却缺乏类似明确的方法论,因此其获取知识的合理性与可靠性也受到质疑。最初这种争端就表现为“两种文化”争论,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启蒙时代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从狄德罗对“机械艺术”(MechanicalArts)的推崇就已经初见端倪。而在英国,早在年,托马斯·赫胥黎(T.H.Huxley)就以“科学与文化”为题探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教育格局的影响。他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争执发生在推崇古代经典的学者与提倡现代文学的学者之间,然而在近三十年,这一情况因为第三方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复杂,那就是自然科学”。作为科学家的赫胥黎自然是提倡在教育中应该给与自然科学足够的重视,并将“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看做是“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与赫胥黎的观点不同,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在年的“文学与科学”讲座中则指出教育重点已经向自然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倾斜,并且他不赞同赫胥黎将科学与文化分开的做法,认为文化既包含文学也包含科学,因此自然科学取代人文学科成为教育的重心是有失偏颇的。在赫胥黎与阿诺德之后,关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年生物化学家约翰·霍尔丹(J.B.S.Haldane)与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就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进程之间的关系展开辩论。在同一年,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也掀起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学术争论,同样是探讨科学理性与价值的整合问题。随后理查兹(I.A.Richards)在《科学与诗》(ScienceandPoetry,)中从语言角度探讨了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并尝试将科学方法引入文学批评实践。科学与人文之争沉寂近半个世纪后,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重新提及这一话题。斯诺对“两种文化”的探讨实际上更多的是想将科学也拔高到与伟大文学相同的地位,他认为“从智识深度、复杂性和表达来说,物质世界的科学大厦同样是人类思想最优美、最精彩的作品”。利维斯(F.R.Leavis)与斯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文学艺术有高于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改变物质世界上,而人之为人的根本却是科学和技术所不能触及的,因此科学之外的东西,如文学、语言,以及“心灵最深处的鲜活本能才是人性的根本,也是一切科学实践的基础”。在此之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Huxley)的《文学与科学》(ScienceandLiterature,)、马丁·格林(MartinGreen)的《科学和卑微的诗学副手》(ScienceandtheShabbyCurateofPoetry,)、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JacobBronowski)的《科学与人类价值》(ScienceandHumanValues,)、诺贝尔奖科学家彼得·梅达沃爵士(SirPeterMedawar)以及科幻作家约翰·布罗克曼(JohnBrockman)等纷纷就这一问题发表见解加入论战,将科学与人文之争重新拉回到大众视野里。 从“两种文化”之争的历史和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其探讨的问题有越来越具体的趋势。早期赫胥黎与阿诺德表面上是探讨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教育中的布局问题,实际上是从宏观层面探讨科学与人文二者在获取知识和真理上孰优孰劣的问题。后来的评论者则开始从更为具体的层面去剖析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如科学与文学、科学与伦理、科学与诗、科学与文学批评等。虽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细致和深入,但是其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科学真理”与“诗性真理”谁才是更高真理的问题。为科学辩护的一方给出了“理性”“科学方法”和现实的证据等论据来支撑其论断,而人文阵营却缺少这样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支撑。正如诺里斯(ChristopherNorris)所说:“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有着严格的、墨守成规的分界线,或者说,这种僵硬的分界线存在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前者被看做是一种可以通过有严格标准的探索方式来佐证的知识模式,而后者则是创造性和想象自由的代表”。面对科学阵营的步步紧逼,人文阵营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如法炮制地尝试将理性与科学方法引入人文学科,对于这一趋势,巴特莱(WilliamBartley)指出: 在文学与艺术中,关于科学‘描述性意义’与‘情感意义’之间的区分一度成为一代文学批评实践的模式与专研问题。不仅如此,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心理分析这一高度自省式的领域,诸如此类的方法论问题被反复提及,试图借此实现从神话到科学的跃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历史学领域”。 与上述将科学引入人文,将“人文”科学化的做法不同,另一种趋势则是将人文凌驾于科学之上,甚至将“科学”人文化。这部分人坚持“诗性真理”高于“科学真理”的看法,认为科学理性和纯粹的经验证据在人类生命体验中有许多无法触及的领域,并试图证明想象、直觉等非理性的元素也在科学发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科学与科学知识本身也只不过是人类主观“文化建构”的产物。“两种文化”的争论甚嚣尘上,年的“索卡尔事件”(SokalHoax)标志了这一争端的顶峰,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与人文两大阵营新一轮论战的开始,这便是学术界有名的“科学大战”(ScienceWars)。 实际上,从“两种文化”之争到后来的“科学大战”,无论是早期对知识优先权的争夺,还是后来出现的人文“科学化”和科学的“人文化”趋势,都是科学与人文之间划界不清晰所带来的后果。因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与巴特莱相似的问题,即“到底有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确定的方法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活动的界限在哪里?理性活动的界限又在哪里?非科学活动是否也有其既定的适用领域?这些领域的归属如何,我们如何对其进行划分、讨论和评估?”这些问题涉及到科学与人文本体论上的探讨,解决这些问题也成为厘清科学与人文本质和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如巴特莱所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活动,包括宗教、哲学,以及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都试图通过将自身与‘科学’进行对照和对比来定义和描述自身。因此,对于科学的本质和科学是什么的先在理解便成为其他学科理解自身的一个先决条件。 由此可见,如何定义“科学”,明白科学的本质,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无论是对科学本身,还是对其他学科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就是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所探讨和试图解决的。只要解决了“划界问题”,不仅解决了科学自身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如巴特莱所说,也会解决其他学科对自身的定位与理解问题。 然而,要解决“划界问题”绝非易事,这一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哲学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是以划界问题为主线,形成了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哲学几个发展阶段”。逻辑实证主义作为西方科学哲学的第一个流派首先提出了“可证实性”(verification)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逻辑实证主义在解决该问题上提出的理论远称不上完善,但是它对“划界问题”的意义和影响却非常深远,因为此后的科学哲学家的“划界问题”理论几乎都是以其为起点和对照。随后卡尔·波普则提出了“可证伪性”(falsification)的标准,认为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科学的可证伪性。此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和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和拉里·劳丹(LarryLaudan)等都从各自的理论出发提出了对“划界问题”的看法。尽管对“划界问题”的探讨层出不穷,然而各派理论却很难达成一致,因此“划界问题”至今仍是科学哲学领域的未解的难题,各派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 从“两种文化”到“划界问题”,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与关系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这些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争议性就是营造戏剧冲突的理想素材。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创作了多部与科学相关的戏剧。《跳跃者》《阿卡迪亚》和《艰难问题》这三部戏剧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划界问题”进行了探讨。斯托帕德是第一位深入和系统思考“划界问题”的剧作家,从《跳跃者》中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批判,到《阿卡迪亚》和《艰难问题》中对科学的认知边界的思考,这些都与“划界问题”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划界问题”悬而未决才导致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出现界限不明晰、不能各司其职,甚至使科学与非科学出现了对立的情况。因此,斯托帕德回到了巴特莱提出的“划界问题”的关键所在,即“到底有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确定的方法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科学活动的界限在哪里?理性活动的界限又在哪里?非科学活动是否也有其既定的适用领域?这些领域的归属如何,我们如何对其进行划分、讨论和评估?”在斯托帕德的这三部剧中,他都是围绕“划界问题”的争论来探讨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而这三部剧作实际上是一个层层深入和寻找答案的过程。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和影响 《跳跃者》一剧并不涉及具体的科学理论,它从整体上探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关系,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界不合理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该剧对“划界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批判展开:逻辑实证主义对“划界问题”的处理走向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极端,而分析哲学则是迎合实证主义唯科学论的划界标准所产生的哲学怪胎。逻辑实证主义将“可证实性”作为科学的权威标准,“认为科学是建基于经验的唯一确实可靠知识。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能否为经验证实就是区分科学与各种非科学的绝对标准”。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否定了形而上学、宗教、艺术等非科学领域获取知识的可靠性和合法性,从而将这些非科学范畴的学科从知识领域中驱逐,走向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极端。 逻辑实证主义对“划界问题”的处理过分绝对,将科学作为最高真理凌驾于其他所有学科之上,而把“非科学”等同于“伪科学”来对待。在这一划界标准之下,“科学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哲学和宗教都要向科学让位”。于是形而上学、伦理学、宗教甚至传统的哲学都被认定为伪科学,使科学与非科学对立起来。逻辑实证主义过分绝对的划界标准所带来的后果使本来就不属于科学领域的哲学、宗教等需要为自身的“科学性”辩护,从而摆脱“伪科学”的帽子。对此,保罗·萨伽德指出:“逻辑实证主义者用两个范畴来进行划界:科学是好的,形而上学是坏的……但二者之间还有一个‘非科学’领域,文学批评、美学等等就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打着科学幌子的伪科学。”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剧中的分析哲学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唯科学论划界标准所催生的产物,它以“科学”来标榜自身,并极力为自身的“科学性”辩护,试图与以往的哲学传统划清界限,将哲学彻底“科学化”。分析哲学的做法无疑是受到科学至上思想的影响,以科学之名装点自身,将两种不同学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种不同学科的界限,而这也正是“划界问题”不清晰所带来的后果。 《跳跃者》对“划界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通过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实现的。该剧于年在伦敦老维克剧院(TheOldVic)首演以来,一直颇受哲学家们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siteera.com/bstefz/7566.html
- 上一篇文章: 重磅预告来自莫扎特故乡的萨尔茨堡爱乐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